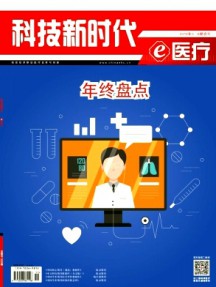人類學(xué)的意義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間:2024-02-19 15:12:16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dú)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人類學(xué)的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摘要】人類學(xué)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同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有許多相通之處。人類學(xué)是研究人、人類文化以及人類社會的起源、成長、變遷及進(jìn)化過程的一門學(xué)問。從人類學(xué)的視角來分析,紀(jì)錄片的文化意義主要反映在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guān)懷、促使人類在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反思與自省以及內(nèi)心對“他者”和“他文化”的理解與尊重等方面。人類學(xué)的這種整體論視角給紀(jì)錄片的主題選擇及拍攝方法提供了諸多啟示,從而使紀(jì)錄片的文化意義更為深刻。
關(guān)鍵詞 紀(jì)錄片 人類學(xué) 文化
一、紀(jì)錄片同人類學(xué)的淵源
從時間上看,人類學(xué)的誕生同影視的出現(xiàn)幾乎同步。世界上第一個電影短片是由盧米埃兄弟于1895 年拍攝的《火車進(jìn)站》,而被視為現(xiàn)代人類學(xué)開端的是英國人阿爾弗雷德·科特·哈登于1898 年前往托雷斯海峽進(jìn)行的民族志考察,在對該區(qū)域進(jìn)行的最廣泛意義上的人類學(xué)研究中,他們將攝影機(jī)也納為記錄的主要手段之一。20 世紀(jì)30 年代美國人類學(xué)家格里哥利·本特森和馬格麗特·米德在巴厘人村莊從事田野調(diào)查時,開始有意識地將紀(jì)錄片同人類學(xué)研究結(jié)合起來。但是,在過去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里,一些人類學(xué)家只是把影像作為在田野調(diào)查中的一種輔助工具,這種片面強(qiáng)化影像工具屬性的態(tài)度會導(dǎo)致我們只強(qiáng)調(diào)影像的記錄功能而忽略其更重要的文化功能。
人類學(xué)是研究人、人類文化以及人類社會的起源、成長、變遷及進(jìn)化過程的一門學(xué)問。同時,紀(jì)錄片是以人類社會中的真實(shí)生活為創(chuàng)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xiàn)對象,并對其進(jìn)行藝術(shù)加工,以展現(xiàn)真實(shí)為本質(zhì),并用真實(shí)來引導(dǎo)人們思考的影視藝術(shù)形式。紀(jì)錄片的這種對人類社會的關(guān)懷和思考,恰與人類學(xué)的研究宗旨不謀而合,這就注定了紀(jì)錄片必然會反映出人類學(xué)的文化意味。例如1923 年公映的《北方的納努克》被認(rèn)為是經(jīng)典紀(jì)錄片的開山之作,由鏡頭所記錄下的原始族群的生活方式、漁獵習(xí)慣以及文化信仰,反映出拍攝者強(qiáng)烈的人文關(guān)懷。反之,人類學(xué)家也同時意識到光影結(jié)合的這種攝影技術(shù)在田野調(diào)查、資料保存方面的表現(xiàn)空間是傳統(tǒng)的文字或圖片所無法比擬的。
于是,人類學(xué)家開始自覺運(yùn)用紀(jì)錄片來體現(xiàn)人類學(xué)的理念,例如法國人類學(xué)家讓·魯什倡導(dǎo)的“真實(shí)電影”在拍攝過程中強(qiáng)調(diào)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相互作用,以期在二者之間建立起了解、互信的關(guān)系。對這種“共享的人類學(xué)”成功運(yùn)用的典范是1960 年由人類學(xué)家和社會學(xué)家合作拍攝而成《夏日紀(jì)事》。
二、紀(jì)錄片的文化意義
在對文化進(jìn)行研究的過程中,人類學(xué)偏向使用整體論的視角來觀察社會,從整體論出發(fā),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各種文化現(xiàn)象之間都存在著必然互動的聯(lián)系,所以不能以孤立的態(tài)度觀察事物,而必須將其置于自然和社會和諧統(tǒng)一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唯其如此,才能對研究對象有一個合理并深刻的了解。這一原則反映出了人類學(xué)對人類生存狀態(tài)的研究熱情和深切關(guān)懷。人類學(xué)的這種整體論視角給紀(jì)錄片的主題選擇及拍攝方法提供了諸多啟示,從而使紀(jì)錄片的文化意義更為深刻。
1、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guān)懷
從人類學(xué)發(fā)展歷程來看,盡管其研究在初期帶有較為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和獵奇的心態(tài),但在學(xué)科逐漸發(fā)展、成熟的過程中,其研究視角在不斷下移,伴隨著對殖民主義、社會達(dá)爾文主義以及種族主義的批判,人類學(xué)家將更多的研究熱情投向了弱勢群體,體現(xiàn)出了明確的對弱勢群體關(guān)懷的傾向。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guān)懷已成為當(dāng)前人類學(xué)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價(jià)值觀念。
人文關(guān)懷的核心內(nèi)容是以人為本,重視每個生命體的平等與尊嚴(yán),發(fā)現(xiàn)每個生命體的存在價(jià)值與意義,從而實(shí)現(xiàn)個體與自然、個體與社會以及個體自我身心發(fā)展的和諧。對于紀(jì)錄片來說,這種人文關(guān)懷的情懷應(yīng)該是其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核心和靈魂,有很多創(chuàng)作者因此將鏡頭集中在了對諸如少數(shù)民族、殘障人群、身心頑疾患者、婦女兒童、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關(guān)注上,以此呼喚主流社會對他們的關(guān)注以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
《舟舟的世界》講述了一位19 歲的先天愚型患者——舟舟。他雖然沒有文化,但很有修養(yǎng);雖然不用為自己的行為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但具有良好的自我約束能力。舟舟對音樂不帶任何功利的熱愛激發(fā)了觀眾發(fā)自內(nèi)心地對生命的尊重。片子明確表示“一切生命都具有尊嚴(yán)”,“舟舟是一個怎樣的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們是否能將他作為與自己一樣的人來對待。”從這部紀(jì)錄片中我們感受到拍攝者將弱勢群體放在一切生命平等地位的深切關(guān)懷之情。
除此之外,記錄癌癥患者生命拼搏的《呼喚》和《壁畫后面的故事》,表現(xiàn)出人類在死亡面前極力維護(hù)的生命尊嚴(yán)。《生命的編織》將鏡頭對準(zhǔn)了28 位聾啞學(xué)生,通過努力地學(xué)習(xí),他們都可以編織出各具特色的藝術(shù)品,令人驚嘆的是,他們憑著生命的激情與堅(jiān)韌,費(fèi)時兩個半月,用2500公斤青麻編織出了當(dāng)時已知的最大的編織藝術(shù)品——《中華根》,他們用奇跡捍衛(wèi)了自己生命的尊嚴(yán)。
2、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反思與自省
文化得以不斷進(jìn)化的原因在于,它服務(wù)于人類的基本需要,展現(xiàn)出每個人都置身其中的可以預(yù)測的世界,從而讓人們真正了解所生存的環(huán)境。①一種文明如果想要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得以保存和延續(xù),就一定要確保其關(guān)鍵性的信息和元素得到傳承。亨廷頓認(rèn)為,“文化的核心包括語言、宗教、價(jià)值觀、傳統(tǒng)以及習(xí)俗。”而這些核心元素的傳承是需要每一代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同過去和未來的幾代人在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宗教習(xí)俗等方面的結(jié)合才能得以實(shí)現(xiàn)的。正如基辛所說:“學(xué)習(xí)鏈條上的任何一個斷裂都可能導(dǎo)致文化的消失。”②
一部紀(jì)錄片的拍攝就是為一段曾經(jīng)確實(shí)存在的歷史留下鮮活的證據(jù),從這個意義上講,紀(jì)錄片是具有文獻(xiàn)資料性質(zhì)的,它能夠忠實(shí)、客觀地記錄鏡頭中社會的發(fā)展變遷,所以其所蘊(yùn)藏的史料價(jià)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紀(jì)實(shí)影像,它不應(yīng)該只具有文獻(xiàn)史料的價(jià)值,更重要的價(jià)值應(yīng)該體現(xiàn)為引導(dǎo)人類反思與自省。文化的希望恰恰就存在于人類的不斷反省之中。
很多紀(jì)錄片的主題都是有關(guān)文化變遷的。關(guān)于文化變遷,人類學(xué)家C·恩伯和M·恩伯認(rèn)為,一種新觀念或新行為可能產(chǎn)生于社會內(nèi)部,也可能是從另一個社會借取而來或由另一個社會所強(qiáng)加的。新觀念和新行為有可能變成文化的觀念或行為,得到人們廣泛的接受,因?yàn)槿藗兌嗌偈亲栽附邮艿模捕嗌倏赡軒в袕?qiáng)制性。③我們從當(dāng)今世界范圍內(nèi)一些少數(shù)民族文化消亡在強(qiáng)勢文化浪潮的侵襲中的現(xiàn)象,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一種文化必定會伴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生變遷,這種變遷可能是和其他文化交融,也可能是走向消亡。如果一種文化拒絕新鮮事物、拒絕信息文化的交流,固化傳統(tǒng)一定會導(dǎo)致文化的消亡。而紀(jì)錄片的使命除了保存消亡文化的遺跡之外,更重要的是從中引導(dǎo)人們反思:是什么原因?qū)е逻@些曾經(jīng)的主流文化被逐步邊緣化直至消失,我們應(yīng)該怎樣辯證地看待這些文化現(xiàn)象,在全球化過程中應(yīng)如何看待文化的變遷造成民族認(rèn)同的變化等等問題。通過文化反思與自省,我們應(yīng)該認(rèn)識到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歷程中,應(yīng)如何超越自我、凈化自我、解放自我。紀(jì)錄片《神鹿啊,我們的神鹿》講述了鄂溫克族傳統(tǒng)文化迅速消亡的事實(shí),以及在這一消亡過程中反映出的人性異化與反異化的抗?fàn)幣c迷惘。紀(jì)錄片深刻地反映出文明一體化進(jìn)程對多元文化的快速吞噬,以至于人們在文化變遷過程中感到迷惘、痛苦,而這實(shí)際上是人性的異化和反異化的一種表現(xiàn)。如何適應(yīng)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以積極主動的姿態(tài)改造傳統(tǒng)文化、接納融入新文化,是此類紀(jì)錄片所帶給我們的深切反思。
3、內(nèi)心對“他者”文化的敬畏
從研究視野和調(diào)查方法而論,人類學(xué)是一門研究“他者”的文化,體現(xiàn)的是對“他者”、“他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因?yàn)槿祟悓W(xué)通常是將研究視線下移到弱勢的、底層的、邊緣的群體,只有在調(diào)查研究過程中以平等的態(tài)度去看待研究對象,發(fā)自內(nèi)心地尊重研究對象——“他者”的生活方式、文化習(xí)俗,才能從對“他者”的理解中獲得對“自我”的反思。
在人類學(xué)田野調(diào)查中有兩組既對立又相關(guān)的視角——“我”與“人”、“我群”與“他者”。我既用我的眼光去觀察他者的文化,也從他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文化;我既看他怎么理解他的文化,也看他者怎么理解我的文化,同時也通過他者的文化和他者的目光來反思自己的文化。④人類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文化相對論”,批判“民族中心論”,強(qiáng)調(diào)歷史上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所有文化在價(jià)值意義上都是平等的,不能以“我群”文化來理解和評判“他者”文化。人類學(xué)的這種“他者”觀察視角在很多紀(jì)錄片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戲班》、《流年》、《木偶兩代人》、《影人兒》等紀(jì)錄片,都將視線集中在木偶戲、皮影戲、剪紙、戲曲等瀕臨滅絕的一些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上,表現(xiàn)出了強(qiáng)烈的保護(hù)民族文化、維護(hù)文化生態(tài)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感。
此類紀(jì)錄片的意義在于迫使人們思考,面對那些現(xiàn)代科技含量較低的傳統(tǒng)文化,如何應(yīng)對才是對其真正的保護(hù)。同時也應(yīng)明確,在現(xiàn)實(shí)的文化一體化浪潮沖擊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都應(yīng)當(dāng)相互容忍、理解、贊賞。
結(jié)語
紀(jì)錄片同人類學(xué)的結(jié)合得以使影像具備了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價(jià)值,從而彰顯出生命的尊嚴(yán)、文化的平等以及對“他者”的敬畏。但同時不可忽視的一個現(xiàn)象是,少數(shù)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為了追求所謂強(qiáng)大的藝術(shù)感染力,而在拍攝選材上故意偏頗,這就失去了我們對客體的事實(shí)尊重,破壞了整體論的立足點(diǎn)。雖然鏡頭中的事實(shí)是客觀存在的,但那只是一種局部的真實(shí)而非本質(zhì)的真實(shí),這就會大大削弱其文獻(xiàn)史料價(jià)值和文化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①②拉里·A·薩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閔惠泉、王緯、徐培喜等譯:《跨文化傳播》[M].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35、43
③C·恩伯,M·恩伯著,杜彬彬譯:《文化的變異——現(xiàn)代文化人類學(xué)通論》[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531
④盤旋,《人類學(xué)視閾下的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D].中央民族大學(xué),2011:81
篇2
關(guān)鍵詞 藝術(shù)學(xué) 藝術(shù)人類學(xué) 藝術(shù)真理 核心理念
一
在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和美學(xué)的歷史上,藝術(shù)的真理問題歷經(jīng)尼采、海德格爾、阿多諾等哲學(xué)家的思考和開掘早已大有氣象,雖然亦難免有陷入理論困局的跡象,不過問題本身總歸處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遺憾,藝術(shù)人類學(xué)家對藝術(shù)的真理這個疑難問題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從心,長期以來幾乎采取了集體回避和隱退的姿態(tài)。在萊頓(R. Layton)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徹(E. P. Hatcher)的《作為文化的藝術(shù):藝術(shù)人類學(xué)導(dǎo)論》(1985年首版)和蓋爾(A. Gell)的《人類學(xué)的藝術(shù)》(1999年首版)等這樣一些帶有總體性或通論性的代表論著中,藝術(shù)的真理問題明顯缺席,在諸如音樂人類學(xué)、視覺人類學(xué)等藝術(shù)人類學(xué)分支學(xué)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國當(dāng)代音樂人類學(xué)家布魯諾·內(nèi)特爾(Bruno Nettl)的名著《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三十一個問題和概念》(2004年修訂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別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樂學(xué)的諸多重要問題和概念,可謂氣勢恢宏,但人類音樂的真理問題還是無緣受到關(guān)注。
推究起來,藝術(shù)人類學(xué)家在藝術(shù)真理問題上的這種幾乎是集體退卻的姿態(tài)和事實(shí),固然有諸多原因,但藝術(shù)人類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的特定歷史階段往往有其相應(yīng)的問題領(lǐng)域的選擇或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貝爾(E. A. Hoebel)在哈徹《作為文化的藝術(shù):藝術(shù)人類學(xué)導(dǎo)論》一書的“序言”里曾頗為中肯地指出,在處理將人類學(xué)理論應(yīng)用于藝術(shù)這件事情上,哈徹的著作與其說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 up to date),倒不如說是在檢驗(yàn)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檢驗(yàn)的重點(diǎn)還只是“原始藝術(shù)”這一概念及其相關(guān)的問題,指證藝術(shù)人類學(xué)領(lǐng)域稱為“原始藝術(shù)”的討論自1970年以后就已經(jīng)從考慮“原始的”一詞轉(zhuǎn)向考慮“藝術(shù)”一詞,其“新的興趣點(diǎn)集中在該詞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義的、是否應(yīng)當(dāng)被應(yīng)用于那些沒有這樣一個詞的民族的活動中去、它又該如何界定這樣一些問題上”②。
相比之下,蓋爾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理論明顯要新銳一些,激進(jìn)一些。他不但意識到藝術(shù)人類學(xué)要關(guān)注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贊同和藝術(shù)人類學(xué)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學(xué)先入之見決裂”,而且認(rèn)為“美學(xué)方法的平庸并沒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現(xiàn)出來”③,例如布爾迪厄(P. Bourdieu)的唯社會學(xué)論實(shí)際上從未考慮藝術(shù)品本身,而僅僅考慮藝術(shù)品表示社會差別的能力,如此等等。不過,蓋爾的此類觀點(diǎn)盡管出現(xiàn)在20世紀(jì)90年代,但在他試圖與之“決裂”的西方美學(xué)理論和觀念清單上,藝術(shù)的真理觀問題還是未能直接進(jìn)入其中,因而也照例無意把藝術(shù)真理問題納入藝術(shù)人類學(xué)視野。這似乎又表明,對藝術(shù)真理問題的回避或忽視與藝術(shù)人類學(xué)學(xué)科的發(fā)展處于何種歷史階段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不管怎么說,這種集體性的回避和退卻已成事實(shí),它畢竟在藝術(shù)人類學(xué)本身的問題鏈上留下了一個根本性的缺環(huán),甚至可以說是藝術(shù)人類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理念滯后的一種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徹出版《作為文化的藝術(shù):藝術(shù)人類學(xué)導(dǎo)論》一書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頗具地震效應(yīng)的、在西方人類學(xué)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xué)與政治學(xué)》。該書編者之一克利福德(J. Clifford)旗幟鮮明地為該書撰寫了題為“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s)的導(dǎo)言,在他看來,民族志的寫作至少受到語境、修辭、制度、文體、政治和歷史上的決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稱民族志為虛構(gòu)(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質(zhì)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約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該書的論題并未有意識地正面應(yīng)對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部分真理”問題,而編者也坦承該書的人類學(xué)偏見使它忽視了對攝影、電影、表演理論、紀(jì)錄片藝術(shù)、非虛構(gòu)小說等藝術(shù)文本的關(guān)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藝術(shù)真理問題在西方藝術(shù)人類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中的總體處境,所以,我們確乎有理由認(rèn)為,藝術(shù)的真理問題(哪怕是所謂的“部分真理”問題)對藝術(shù)人類學(xué)學(xué)科來說還是一個新鮮的疑難話題。這樣,盡管在《寫文化》出版十多年后問世的《寫文化之后》一書的編者判定《寫文化》已逐漸被看作是一部“有幾分像人類學(xué)思想上的分水嶺”⑥那樣的書,但就藝術(shù)真理問題而言,這條分水嶺實(shí)質(zhì)上并沒有清晰地綿延到西方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田園之中。
關(guān)于藝術(shù)的真理問題,我在1999年中國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會成立之際所撰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與知識重構(gòu)》一文中曾把該學(xué)科的一個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問藝術(shù)真理的學(xué)術(shù)知識生產(chǎn)運(yùn)動”,隨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講又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這樣一門立足于人類學(xué)的立場和方法、從藝術(shù)的角度研究人的學(xué)科是一種新式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它不僅僅是關(guān)于“原始藝術(shù)”的,“不僅僅是關(guān)于‘藝術(shù)’的,也不僅僅是關(guān)于‘藝術(shù)’的感性學(xué)或某種新的知識論,而且還是一種人類學(xué)立場上的藝術(shù)真理論”⑦。本文擬針對上文所闡述的問題情境,對我所主張的“完全的藝術(shù)真理觀”這一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嘗試性的闡述。
二
事實(shí)上,我們一旦把藝術(shù)真理問題引入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議事日程,首先就會真切地體會到類似于法國哲學(xué)家保羅·利科所表述的那種復(fù)雜心情和態(tài)度取向:“一方面,各種哲學(xué)相繼出現(xiàn),相互矛盾,相互詆毀,使真理看上去是變化的,在這種情況下,哲學(xué)史是懷疑主義的課程;另一方面,我們向往一種真理,精神之間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標(biāo)準(zhǔn),至少也是其標(biāo)志。”⑧不過,如此鮮明的態(tài)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來給克利福德所標(biāo)舉的“部分真理”說作出屬性判斷。因?yàn)檫@一民族志寫作的理念確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敘述的真理(the truths of cultural accounts)所遭逢的語言、修辭、權(quán)力和歷史諸方面帶來的不確定性或偶然性,這對文化敘述的真理的復(fù)雜性和豐富性無疑是一種尊重,一種張揚(yáng),因而我們也確乎不能說這種“部分真理”說只是在簡單地修讀“懷疑主義的課程”;但克利福德同時又聲稱:“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們不再會認(rèn)識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稱接近它”⑨,這顯然是急劇地朝著極端的文化相對主義甚或懷疑主義的方向挪步,并終將稀釋和失落“部分真理”說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義。
由此,我們不難推想,如果藝術(shù)人類學(xué)家在面對紛繁復(fù)雜的人類藝術(shù)現(xiàn)象和藝術(shù)史的時候,無意把藝術(shù)人類學(xué)與藝術(shù)真理問題勾連起來,無意警惕和克
服極端的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的理論迷霧,無心打造甚或自動放棄種種尋求藝術(shù)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轉(zhuǎn)而簡單地移植或運(yùn)用迄今仍被許多西方人類學(xué)家所信奉的、隨時有可能走得太遠(yuǎn)的“部分真理”說,那么,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工作的意義本身很可能就會大打折扣。 其實(shí),在這一關(guān)鍵點(diǎn)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種有力的印證:“我在這篇‘導(dǎo)言’中一直極力主張的那種不完全性(partiality)總是預(yù)先假定了一個地方性歷史的困境”⑩,并聲稱自己的這種歷史主義觀念應(yīng)大量地歸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但在各種“地方敘事”(local narratives)和它們的替代物亦即“主導(dǎo)敘事”(master narrative)之間并沒有接受后者。在我看來,這里所假定的這種“地方性歷史的困境”同時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說所要面臨的困境,而其內(nèi)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與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所倡導(dǎo)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邏輯上預(yù)設(shè)了非“地方性知識”或非“地方性歷史”的存在,而它們事實(shí)上指的是西方知識或西方歷史;二是在這種非“地方性知識”或非“地方性歷史”中,依然隱含地指稱存在著優(yōu)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價(jià)值。(11)由此,我們不難體會到“部分真理”說背后所潛藏著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論意味的理論指向。
這樣,在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設(shè)計(jì)和選擇上,我們與其在那種“部分真理”說的萬花筒里端詳藝術(shù)真理的種種局部的、變幻莫測的容貌,還不如明智地選擇有望在“一”與“多”之間、在完全性與不完全性之間進(jìn)行平等貫通和整合的一種完全的藝術(shù)真理觀。
那么,圍繞新式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撐呢?我認(rèn)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把研究范圍推及全景式的人類藝術(shù)來達(dá)成藝術(shù)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主要研究無文字社會的藝術(shù),以及文明社會里的民間藝術(shù)或少數(shù)民族的藝術(shù)傳統(tǒng)。新式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盡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圍推及全景式的人類藝術(shù),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統(tǒng)內(nèi)的藝術(shù)作為自己的合法的關(guān)注對象。如果還是繼續(xù)像從前那樣主要研究無文字社會的藝術(shù),而此類社會的很多藝術(shù)形態(tài)都已經(jīng)消失,而且有些還在隨時隨刻地消失,那么,這個學(xué)科可以研究的東西事實(shí)上是走向萎縮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上逼近人類藝術(shù)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我們才有望在各種或大或小的藝術(shù)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藝術(shù)真理的訊息,而因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的對象總有其實(shí)在性和情境約定性,所以,在藝術(shù)真理的敘述或書寫上即便需要某種“想象”或“虛構(gòu)”的詩學(xué),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約定才能順利敘述或書寫的情境非約定性因素,但它們本身并不能改變藝術(shù)真理在總體指向上的確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為文化的藝術(shù)”這一藝術(shù)觀念總譜中努力尋求藝術(shù)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已經(jīng)有一個變化,注意力開始從“美的藝術(shù)”(fine arts)轉(zhuǎn)向“作為文化的藝術(shù)”,考察藝術(shù)與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并進(jìn)一步形成了幾個主要的相關(guān)觀念:一個是把藝術(shù)視作“文化的表現(xiàn)”,一個是“作為文化系統(tǒng)的藝術(shù)”,另一個是“作為技術(shù)系統(tǒng)的藝術(shù)”。這和原先美學(xué)里所面對的那個“藝術(shù)”概念相比,顯然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變化和實(shí)質(zhì)性的差別。對此,哈徹的體會頗有代表性。由于在實(shí)際的現(xiàn)代用法中,“藝術(shù)”一詞不再限于雕塑和繪畫,其界定的范圍非常廣泛,并且包括紡織品、人體繪畫、機(jī)遇劇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因此她感到,過去那些狹隘的定義就像它們從前所做的那樣雖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觀點(diǎn),但是,當(dāng)我們試圖從跨文化上來使用“藝術(shù)”觀念時,還是有許多問題,尤其是因?yàn)樵谖鞣轿幕瘋鹘y(tǒng)內(nèi)有許多藝術(shù)定義,并且只有某種非常寬泛的一致意見。因此,“在工業(yè)文明中,當(dāng)藝術(shù)概念在媒介和內(nèi)容方面被放寬到異乎尋常的程度時,至少含蓄地表明藝術(shù)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義已經(jīng)被縮小了,而藝術(shù)與它的(文化)語境之間的關(guān)系也越來越少。這正是那種被當(dāng)作純粹為了審美靜觀、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純粹藝術(shù)、稱為‘藝術(shù)’之物的無用之必要性的藝術(shù)概念。它對跨文化研究來說不是一個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純粹的動機(jī)存在”。(12)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哈徹就把“藝術(shù)”的成分解析為純粹審美(purely esthetic)、技能或技術(shù)(craftsmanship)、意義(meaning)這樣三個層面。而蓋爾在20世紀(jì)90年代試圖從“作為技術(shù)系統(tǒng)的藝術(shù)”(art as a technical system)這樣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觀念上來考察包括原始藝術(shù)和現(xiàn)代藝術(shù)在內(nèi)的各種藝術(shù)的魅力技術(shù)(the 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13)顯然又是一種有效的推進(jìn)。
諸如此類的藝術(shù)觀念群及其相應(yīng)的研究方式或?qū)W術(shù)轉(zhuǎn)向,說明藝術(shù)人類學(xué)已不再把“美的藝術(shù)”作為一個終極性的考察目標(biāo),而是在“作為文化的藝術(shù)”這個觀念總譜的鞭策下,勘探人類藝術(shù)形態(tài)和觀念上的復(fù)雜群落,注重發(fā)掘藝術(shù)與某種具體的文化表現(xiàn)、文化行為和文化技術(shù)之間的普遍聯(lián)系。雖然這里也難免還是有一些藝術(shù)概念上的預(yù)設(shè),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努力把這些預(yù)設(shè)和成分融入一個個情境性的解析過程之中,通過這種解析過程的展開,不斷地反思、檢驗(yàn)和調(diào)整自身的藝術(shù)觀念,讓它們經(jīng)受舊石器時代以來人類各個時期、各個區(qū)域和各個族群的藝術(shù)所構(gòu)成的事實(shí)大熔爐的考量,從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類藝術(shù)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煉藝術(shù)真理的話語,于是,藝術(shù)人類學(xué)在藝術(shù)觀念和藝術(shù)真理的話語問題上的種種“作為”式的語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經(jīng)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禮。當(dāng)然,這種集群式解析的過程性演歷,既要有與解析對象之間充分的情境關(guān)聯(lián),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實(shí)判據(jù),又不排斥解析主體與解析對象之間復(fù)雜的情境性互動,建構(gòu)情境性表達(dá)關(guān)系的空間,從而在藝術(shù)觀念和藝術(shù)真理的復(fù)雜認(rèn)知和書寫的歷史過程性中通過不斷地?fù)P棄不確定性和不完全性來達(dá)成藝術(shù)真理的完全性。
3.在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運(yùn)用那種強(qiáng)調(diào)空間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識,轉(zhuǎn)而強(qiáng)調(diào)非西方藝術(shù)的種種樣式、形態(tài)、意識、觀念和價(jià)值與西方藝術(shù)至少處在理論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國藝術(shù)、日本藝術(shù)和印度藝術(shù)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種“地方性知識”、地方性經(jīng)驗(yàn)和地方性價(jià)值的東西,確切地說,它們各自都是某種情境性的藝術(shù),它們在認(rèn)知自身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表達(dá)自身的藝術(shù)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歷史過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約定、情境內(nèi)涵,因而和西方藝術(shù)一樣有其自身獨(dú)特的價(jià)值,具有西方藝術(shù)所無法替代的知識性價(jià)值和真理性內(nèi)容。由于無意把它們置入那種依然隱性地帶有西方知識至上和西方價(jià)值優(yōu)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識”的陰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隨著新式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的不斷推展,歷代的東方藝術(shù)和世界上各種小型社會的藝術(shù)都將有望被視作一個個在藝術(shù)的真理性內(nèi)容上具有足夠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類學(xué)田野調(diào)查和民族志書寫的一個個帶有被壓迫意味的對象。于是,這樣一些獨(dú)特的藝術(shù)世界就有可能被賦予自呈自現(xiàn)、自我決斷的機(jī)理,從而在一定的現(xiàn)實(shí)性上和西方藝術(shù)世界之間形成一種互為他者、雙向乃至多向制導(dǎo)的全景式機(jī)制,讓藝術(shù)真理的完全性問題在不斷多維化和細(xì)密化的他者之間的互動、對話、交流甚或交變中得以開顯。也就是說,各種藝術(shù)世界的自主、自恰和價(jià)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將在現(xiàn)實(shí)性上強(qiáng)化藝術(shù)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偏重于對藝術(shù)作品的靜態(tài)描述,而忽視對藝術(shù)家的行為以及行為過程的動態(tài)解釋,換句話講就是對藝術(shù)的研究總是習(xí)慣于針對藝術(shù)品本身,而制作、觀看藝術(shù)品的人在研究視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除了繼續(xù)重視藝術(shù)品的解析之外,也關(guān)注人類藝術(shù)活動當(dāng)中的藝術(shù)行為和人的在場(包括藝術(shù)家的在場)這些環(huán)節(jié),力圖對各種文化情境條件下從事藝術(shù)制作、藝術(shù)生產(chǎn)和進(jìn)行藝術(shù)交往的藝術(shù)家、藝術(shù)作品和藝術(shù)行為等整體流程進(jìn)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體的藝術(shù)生產(chǎn)、藝術(shù)交往或藝術(shù)消費(fèi)的完整格局中來全面地考察人類在藝術(shù)需要、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藝術(shù)交往上的真理訴求。
三
篇3
一、作為“學(xué)科”或作為“學(xué)問”
成為學(xué)科或被稱為學(xué)科,應(yīng)該是一件很嚴(yán)肅的事情。盡管人類學(xué)形成于19世紀(jì),但1954年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承認(rèn)為一個學(xué)科,仍然具有標(biāo)志性的意義。即便藝術(shù)人類學(xué)足以成為一個學(xué)科,在目前的中國,這還只是一種可能性而非現(xiàn)實(shí)。談?wù)撍囆g(shù)人類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學(xué)科規(guī)范的合法性,可以指其尚未建成或需要建成一個學(xué)科,或者指的是把藝術(shù)人類學(xué)放在文化人類學(xué)這樣的學(xué)科下建設(shè)和規(guī)范,而不是說藝術(shù)人類學(xué)已然成為一個學(xué)科。大概因此,有的學(xué)者將藝術(shù)人類學(xué)稱為文化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分支,有的學(xué)者更愿意選擇“人類學(xué)藝術(shù)研究”這一說法而非“藝術(shù)人類學(xué)”①———末尾的“學(xué)”字容易引起爭議。人類學(xué)的藝術(shù)研究與社會學(xué)的藝術(shù)研究、哲學(xué)的藝術(shù)研究、宗教學(xué)的藝術(shù)研究、心理學(xué)的藝術(shù)研究,構(gòu)詞法和用意類似,均是將各具特色的藝術(shù)研究放在特定學(xué)科下看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xué)科分類與代碼表(國家標(biāo)準(zhǔn)GBT13745-2009)》中,除人類學(xué)的藝術(shù)研究外,上述其他學(xué)科的藝術(shù)研究都已獲得二級或三級學(xué)科代碼,從而成為藝術(shù)社會學(xué)、藝術(shù)美學(xué)、宗教文學(xué)藝術(shù)(以及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藝術(shù))、藝術(shù)心理學(xué)。藝術(shù)人類學(xué)在將來完全有可能被認(rèn)可成為學(xué)科,在此之前,我們可以把藝術(shù)人類學(xué)理解為一種與藝術(shù)和人類學(xué)有關(guān)的特定“學(xué)問”。學(xué)術(shù)時勢和學(xué)科精英的造就,使文化人類學(xué)在當(dāng)今中國漸呈顯學(xué)之態(tài)(至少在某些領(lǐng)域)。
與以往偏好思辨的學(xué)科相比,它確能為諸如審美(美學(xué))、藝術(shù)、文化等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形成的熱點(diǎn)重新注入清新的空氣和新穎的方法。在文化人類學(xué)取得進(jìn)展的同時,其他學(xué)科也隨著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的更新而變換姿態(tài)和方法。在劃定各自學(xué)科領(lǐng)地的同時,相互的借用與交叉也就愈發(fā)明顯。相當(dāng)一部分學(xué)者先后接受不同學(xué)科的訓(xùn)練或熏陶,具備跨學(xué)科研究能力和多學(xué)科身份。對于不同學(xué)科的優(yōu)劣長短,他們最為清楚。所以,一方面出現(xiàn)不同含義(不同學(xué)科主導(dǎo))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或?qū)徝廊祟悓W(xué)、文藝人類學(xué)、美學(xué)人類學(xué));另一方面,一種含義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會受到另一種含義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指責(zé)。而且,因?yàn)閷窒扌缘那宄J(rèn)識,指責(zé)有時顯得深刻而尖銳。
藝術(shù)研究的學(xué)科分化與方法更新,不只發(fā)生在藝術(shù)與人類學(xué)之間。就西方學(xué)脈而言,最早觸及藝術(shù)問題的是諸如柏拉圖那樣的哲學(xué)家,而后是研究藝術(shù)問題的美學(xué)(或藝術(shù)哲學(xué))在哲學(xué)中的崛起,再后來就是藝術(shù)學(xué)從美學(xué)中分離,并要求自己獨(dú)立的學(xué)科地位。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藝術(shù)問題被放在美學(xué)的框架內(nèi)討論,另一個從文學(xué)理論中派生出來的學(xué)科———文藝學(xué)(它在《學(xué)科分類與代碼表》中準(zhǔn)確的名字是“文藝美學(xué)”,“文藝學(xué)”應(yīng)是簡稱)也占據(jù)藝術(shù)問題研究的半壁江山。相比起來,藝術(shù)學(xué)的聲音很微弱。一位從文藝學(xué)轉(zhuǎn)入藝術(shù)學(xué)的學(xué)者深有感觸:“厘定藝術(shù)學(xué)的學(xué)科對象與研究領(lǐng)域,除了必須正確處理好藝術(shù)學(xué)與美學(xué)的關(guān)系之外。在我看來,還應(yīng)大致厘定藝術(shù)學(xué)與文藝學(xué)及美術(shù)學(xué)的關(guān)系”,“文藝學(xué)的發(fā)達(dá)又頗有些‘喧賓奪主’的態(tài)勢,歷史悠久、傳統(tǒng)深厚的文藝學(xué)常常顯得似乎足以與初出茅廬的藝術(shù)學(xué)平分秋色”。他設(shè)計(jì)的分配方案是,文藝學(xué)以語言文學(xué)為對象(近乎“文學(xué)學(xué)”),而藝術(shù)學(xué)體系又將文學(xué)(語言藝術(shù))包容進(jìn)來。似乎有了一種逆轉(zhuǎn),不是文藝學(xué)包括藝術(shù)學(xué),而是藝術(shù)學(xué)包括文藝學(xué)。①在學(xué)科分化日趨明顯的時代,討論學(xué)科邊界是必要的,甚至不妨成為具有知識社會學(xué)意義的自反性研究主題。同時,學(xué)科分化及跨學(xué)科的結(jié)果肯定不僅是對正確、正當(dāng)或正統(tǒng)的話語競爭,更應(yīng)該提出關(guān)于學(xué)科合作與主題延續(xù)的建設(shè)性方案。這是跨學(xué)科研究的優(yōu)勢所在,也是跨學(xué)科學(xué)者的優(yōu)勢所在。具體到藝術(shù)人類學(xué),盡管它究竟歸屬于文化人類學(xué)還是藝術(shù)學(xué)(目前看,前者更具主導(dǎo)性②)并非毫無爭議,而爭議也并非毫無意義,但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從美學(xué)、文藝學(xué)或藝術(shù)學(xué)而來的那些概念、命題如何獲得新的生機(jī),如何延展到藝術(shù)人類學(xué)中重新厘定,而不是簡單地加以廢棄。這樣,促使學(xué)科之間形成真正的對話主題而不是自說自話,也使藝術(shù)(而不僅是文化)真正成為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研究焦點(diǎn)。
二、藝術(shù)人類學(xué)與“藝術(shù)”有何距離
從事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的人,大致可能受到兩方面的挑剔。一是被認(rèn)為沒有真正做出文化人類學(xué)的味道(來自文化人類學(xué)界),二是被指所做的研究有藝術(shù)研究之名而無藝術(shù)研究之實(shí),做的是文化研究、民俗研究而非藝術(shù)研究,或者把藝術(shù)對象當(dāng)作民俗文化對象來研究,甚至于研究對象是否可以稱之為藝術(shù)也很牽強(qiáng)(來自藝術(shù)實(shí)踐與理論界)。總之,不通曉人類學(xué)的人進(jìn)行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與不通曉藝術(shù)的人進(jìn)行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其牽強(qiáng)與偏頗程度不相上下。藝術(shù)人類學(xué)作為一種研究(即便是實(shí)證研究)與具體的藝術(shù)實(shí)踐之間可能存在隔膜。與藝術(shù)哲學(xué)和美學(xué)相比,從人類學(xué)立場出發(fā)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想要轉(zhuǎn)變的正是理論形態(tài)的藝術(shù)哲學(xué)和凌駕于藝術(shù)之上的美學(xué)的視角,從而將藝術(shù)(包括藝術(shù)哲學(xué)和美學(xué))放回到與實(shí)際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藝術(shù)世界之中,以尊重當(dāng)事人自己的解釋為前提來解釋藝術(shù),或解釋當(dāng)事人對藝術(shù)的解釋。
從現(xiàn)有藝術(shù)門類看,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對象的種類偏重于造型藝術(shù)、口承文學(xué)、音樂等門類,而忽視其他藝術(shù)門類。這種狀況一方面取決于早期西方人類學(xué)的民族志博物館建制(主要收集有形的、可移動的物品),另一方面也與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者自身藝術(shù)分析能力的局限有關(guān)。還有一種指責(zé),針對的是某些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仍在探討關(guān)于原始藝術(shù)或藝術(shù)起源的過去時話題。現(xiàn)代性和全球化的卷入與沖擊、對社會進(jìn)化論的懷疑以及對知識與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意識,使少數(shù)民族或漢族農(nóng)村的原始主義表述(“活化石”、“原生態(tài)”等)變得十分可疑。改變這種局面的方案,一是把少數(shù)民族或漢族村落的藝術(shù)放在當(dāng)下時間進(jìn)程中審視,將虛擬的過去時轉(zhuǎn)換為現(xiàn)在進(jìn)行時,關(guān)注社會行動者的現(xiàn)實(shí)的訴求和行動的力量。③二是擴(kuò)大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對象范圍,從少數(shù)民族或鄉(xiāng)村到城市、學(xué)院和主流藝術(shù)界,從民族民間俗文化中的藝術(shù)到都市人群、專業(yè)人士的雅文化中的藝術(shù)。④實(shí)現(xiàn)此轉(zhuǎn)變之后,我們進(jìn)而要注意這樣的問題:現(xiàn)在進(jìn)行時的藝術(shù)如何與過去時態(tài)的藝術(shù)相互勾連,因?yàn)槟承﹤鹘y(tǒng)在當(dāng)下的生活場景中有所遺留,而原始主義表述不僅為學(xué)者所用,也被文化持有者或社會行動者所用。在將藝術(shù)人類學(xué)對象由俗而雅地?cái)U(kuò)大時,要覺察雅俗之別和雅俗之間如何轉(zhuǎn)換、流通。#p#分頁標(biāo)題#e#
泰勒時代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或人類學(xué)的藝術(shù)研究,因?yàn)榘阉囆g(shù)主要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來看待而與藝術(shù)學(xué)、美學(xué)或文藝學(xué)意義上的藝術(shù)研究有所隔膜,那么,當(dāng)藝術(shù)人類學(xué)之名和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組織得以成立,藝術(shù)人類學(xué)與藝術(shù)之間隔膜就應(yīng)當(dāng)有所消融。我們應(yīng)當(dāng)在藝術(shù)這個范疇下培養(yǎng)一種真正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意識和眼光,而不是遠(yuǎn)離藝術(shù)來探討藝術(shù)。藝術(shù)學(xué)或美學(xué)意義上的藝術(shù)研究可能使我們看不到藝術(shù)在生活之中,看不到藝術(shù)的社會性與文化性,而離開藝術(shù)的藝術(shù)研究卻使藝術(shù)完全融解在生活之中,成為社會文化的表征,失卻藝術(shù)自身的特性。藝術(shù)是文化,但同時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應(yīng)當(dāng)站在藝術(shù)的角度促使藝術(shù)人類學(xué)進(jìn)入藝術(shù)的世界,因?yàn)?ldquo;藝術(shù)的人類學(xué)研究所面臨的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缺乏一種關(guān)于人類學(xué)視野中的‘藝術(shù)’的整體認(rèn)定”。⑤在辨析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性質(zhì)、為藝術(shù)人類學(xué)進(jìn)行學(xué)科定位之余,我們不得不面對一些最基本的問題: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研究對象是什么?作為藝術(shù)人類學(xué)對象的“藝術(shù)”又是什么?就前一個問題,僅從對象的性質(zhì)看,有的稱為“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研究與稱之為“文化人類學(xué)”或“民俗學(xué)”研究并沒有太大區(qū)別。它的對象也許與“藝術(shù)”這個詞,但其研究視角、概念與藝術(shù)問題有很大距離。就第二個問題而言,盡管自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以來,藝術(shù)的傳統(tǒng)定義日趨模糊,其討論也日趨開放而多元化,充滿哲學(xué)意義和社會文化語境的諸多不確定性,但在斷裂中仍有延續(xù)或某種對應(yīng)性。理解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要把它們放在對抗傳統(tǒng)、超越傳統(tǒng)、與傳統(tǒng)對話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它們關(guān)于藝術(shù)的討論,無論走得多遠(yuǎn),所針對的還是那些最基本的藝術(shù)問題(從基本的藝術(shù)問題出發(fā))。同樣,無論藝術(shù)人類學(xué)具有如何開放的藝術(shù)定義和理解,其出發(fā)點(diǎn)或突破點(diǎn)應(yīng)該是基本的藝術(shù)問題。只有在這些問題及其相應(yīng)的范疇中,藝術(shù)人類學(xué)才能找到自己的藝術(shù)的對象,才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回答“藝術(shù)是什么”這樣的問題,從而與當(dāng)前的藝術(shù)學(xué)或美學(xué)展開有的放矢的合作或針鋒相對的對話。喬治•馬爾庫斯和弗雷德•邁爾斯在《文化交流:重塑藝術(shù)和人類學(xué)》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人類學(xué)與藝術(shù)之間的交流得到鼓勵,藝術(shù)界和人類學(xué)界二者都在尋找自身研究的新主題,因?yàn)樗鼈儌鹘y(tǒng)的研究主題和對象發(fā)生了巨大變化。①霍華德•墨菲和摩爾根•帕金斯在2006年出版的《藝術(shù)人類學(xué)》中認(rèn)為,人類學(xué)“直到最近,還是停留在有關(guān)藝術(shù)定義討論的外面,目前歐美藝術(shù)實(shí)踐的每一部分都已經(jīng)在被熱烈地爭論著,而在這些爭論中,人類學(xué)的思維方式經(jīng)常是對藝術(shù)有影響的。因此,人類學(xué)家應(yīng)該加入這種討論,并做出自己的貢獻(xiàn)”。②
三、進(jìn)入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藝術(shù)問題”
自從1817年黑格爾在海德堡的美學(xué)演講中預(yù)言“藝術(shù)之終結(jié)”以來,經(jīng)典性的藝術(shù)定義、體裁分類、作者主體性、藝術(shù)與生活的界限等等均被動搖。追隨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和“家族相似性”思想而來的古德曼、肯尼克和維茲等人否認(rèn)藝術(shù)的可定義性,古德曼認(rèn)為我們不應(yīng)該問“什么是藝術(shù)”,而應(yīng)問“某物何時何地成為藝術(shù)”。與此相似,喬治•迪基認(rèn)為藝術(shù)之所以為藝術(shù)在于特定的“慣例”(包括藝術(shù)慣例和社會慣例),因而“一件藝術(shù)品就是某人說我叫這個東西為藝術(shù)品的客體”。③伊哈布•哈桑借用巴赫金的“狂歡”一詞描述后現(xiàn)代藝術(shù)體裁混雜、滑稽模仿、言語狂歡等現(xiàn)象,什克洛夫斯基則認(rèn)為“新的藝術(shù)形式的產(chǎn)生是由把向來不入流的形式上升正宗而實(shí)現(xiàn)的”。④在藝術(shù)主體性方面,本雅明探討藝術(shù)的機(jī)械復(fù)制性,福柯、德里達(dá)從不同角度顛覆西方古典時期以來建構(gòu)的人的主體性,羅蘭•巴特從文本自身出發(fā)宣告文本作者主體性的“死亡”。
上述線索和問題,可以重新進(jìn)入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視野和論域。當(dāng)我們在村落情境中討論鄉(xiāng)民藝術(shù)時,當(dāng)我們在人類學(xué)意義上的地方感中討論藝術(shù)與日常生活的關(guān)聯(lián)時,應(yīng)對這些曾經(jīng)“前衛(wèi)”的問題何嘗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傳統(tǒng)的藝術(shù)概念很難對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藝術(shù)現(xiàn)象加以定義、分類和解釋,面對民間藝術(shù)時同樣如此。比如,貴州省的“安順地戲”在當(dāng)?shù)厝朔Q為“跳神”,它的一個傳承人一再強(qiáng)調(diào)“‘地戲’(跳神)不是‘戲’”。⑤張士閃在《鄉(xiāng)民藝術(shù)的文化解讀:魯中四村考察》中事先聲明:“我們將本書所涉及到的小章竹馬、井塘村與東營村的儀式歌、洼子村的‘啦呱’等歸類于鄉(xiāng)民藝術(shù),主要出于對傳統(tǒng)民俗學(xué)、藝術(shù)學(xué)研究分類慣例的遵從,也為行文方便。因?yàn)樵谶@些活動的展演過程中,盡管蘊(yùn)含著大量的藝術(shù)因素,但作為其傳承主體的村民從未視之為‘藝術(shù)’。”⑥正如布洛克就“原始藝術(shù)”所言,“它之所以是藝術(shù),并非是因?yàn)槟切┲圃旌褪褂盟娜苏f它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yàn)槲覀冋f它是”。⑦按照傳統(tǒng)或藝術(shù)院校形成的藝術(shù)概念去理解民間藝術(shù),或?yàn)槊耖g藝術(shù)的體裁分類,將每一個認(rèn)真對待民間藝術(shù)的研究者置于苦惱或?qū)擂蔚木车?找不到恰當(dāng)?shù)脑~來對應(yīng),找不到恰當(dāng)?shù)乃囆g(shù)體裁來歸類,以至于有時我們甚至懷疑民間到底有沒有我們所謂的藝術(shù)或藝術(shù)的種類。
正是在民間到底有沒有藝術(shù)這個問題上,藝術(shù)人類學(xué)要停下來深思。民間是藝術(shù)人類學(xué)研究最初始也是最主要的陣地,“作為藝術(shù)人類學(xué)對象的‘藝術(shù)’是什么”與“民間有沒有藝術(shù)”這個問題直接相關(guān)。西方人類學(xué)對于土著或小規(guī)模社會有無藝術(shù)的討論,有助于回答這一問題。在距今80余年前出版的著作中,羅伯特•路威批評有的人將初民藝術(shù)視為毫無美感可言的“實(shí)用之從仆”,他認(rèn)為“愛美之心,四海相同”,“藝術(shù)的嗜好實(shí)為人性中的若干根深蒂固代遠(yuǎn)年湮的因素之一”,初民也有“為藝術(shù)而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他們當(dāng)中的藝術(shù)家也能夠“以技術(shù)與美感為指歸”。總之,藝術(shù)是人生的一個基本事實(shí),是人與其他生物區(qū)別的重要標(biāo)志。①與此相似,雷蒙德•弗思認(rèn)為,無文字民族具有與西方人共同的審美感知力和判斷力,他們的藝術(shù)品同樣綜合了經(jīng)驗(yàn)想象和情感因素,同樣能夠喚起由線條、色彩和動作引發(fā)的情感回應(yīng),可以稱之為“審美”。②羅伯特•萊頓基本上認(rèn)可弗思的判斷,不僅如此,他認(rèn)為弗思過于“保守”地“將一個民族有關(guān)周圍世界的理念和概念僅看作社會生活的附屬,而沒有把它當(dāng)成經(jīng)驗(yàn)性的有創(chuàng)造力的真實(shí)積累”。③弗思為藝術(shù)分析提出的命題,一是發(fā)現(xiàn)藝術(shù)的生產(chǎn)和使用對其所屬的社會有何影響,二是找出藝術(shù)的形式特征所表達(dá)的價(jià)值的本質(zhì)。在萊頓看來,第二個命題本來具有自身的意義,弗思卻使它完全依附于第一個命題,藝術(shù)作為藝術(shù)的探究也就早早地?cái)嗨土恕;谶@種認(rèn)識,盡管研究的是諸如西非或澳洲小型社會的非西方藝術(shù),萊頓為藝術(shù)人類學(xué)選擇的分析工具和表述框架卻是西方美學(xué)或藝術(shù)哲學(xué)式的,他探討藝術(shù)的定義、美學(xué)與審美傳統(tǒng)、藝術(shù)家的價(jià)值觀與創(chuàng)造力、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多樣性及其形成等似乎不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藝術(shù)人類學(xué)而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藝術(shù)學(xué)、美學(xué)或藝術(shù)哲學(xué)中的話題。與此同時,他回顧與應(yīng)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至潘諾夫斯基、貢布里希等人提出的那些經(jīng)典的美學(xué)或藝術(shù)問題,而泰勒、博厄斯、馬林諾夫斯基等人類學(xué)家提供的例證和觀點(diǎn)則穿梭其間———藝術(shù)(美學(xué))與人類學(xué)就這樣鑲嵌在一起。萊頓的立場很明確:“盡管世界各地的各種文化都創(chuàng)造出了豐富多彩的藝術(shù)形式及內(nèi)容,但這些藝術(shù)家們卻是被某種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問題以及共同的程式所限制與激勵,這些共同性證明了在文化生活的探索過程中存在著一種特別的技能。”④這種特別的技能就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正如王建民在《藝術(shù)人類學(xué)》中譯本后記中總結(jié)的,對于萊頓,如何看待藝術(shù)的審美或者藝術(shù)的形象性是藝術(shù)人類學(xué)的焦點(diǎn)問題。盡管受到另一位人類學(xué)家蓋爾的質(zhì)疑,⑤萊頓的框架有其深刻意義,尤其對于適應(yīng)了用社會結(jié)構(gòu)或文化功能來解釋藝術(shù)而遠(yuǎn)離藝術(shù)問題本身的中國藝術(shù)人類學(xué)而言。#p#分頁標(biāo)題#e#
篇4
關(guān)鍵詞:張藝謀電影;藝術(shù)人類學(xué);民族色彩
中圖分類號:J90-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5-0042-01
從人類學(xué)的研究角度出發(fā),張藝謀的電影蘊(yùn)含這豐富的人類學(xué)內(nèi)涵是他民族和他國家研究中國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人文風(fēng)情、民俗習(xí)慣、民族心理等的重要素材。本文用人類學(xué)的方法對張藝謀的電影進(jìn)行人類學(xué)研究和審視,這是一種多主體的、多指向性的研究,一方面從人類學(xué)角度給張的電影作一個全面的分析,提煉出當(dāng)代中國社會在藝術(shù)文本中的社會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總結(jié)出張藝謀此類電影的特點(diǎn)與不足,在人類學(xué)意義的框架下給中國的電影的發(fā)展給予一點(diǎn)思想性指導(dǎo)。
人類學(xué)視野下的張藝謀電影。人類學(xué)一詞來源于希臘文,是研究人的科學(xué)或解釋為關(guān)于人的研究。英文寫作“Anthropology”,最早見諸于古希臘哲學(xué)家亞里士多德對具有高尚品質(zhì)及行為者的描述中,貫穿人類學(xué)的兩個核心詞語是“文化”和“本源”,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說:“人類學(xué)就是一門關(guān)于‘文化的科學(xué)’”,我國人類學(xué)家林惠祥指出,人類學(xu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實(shí)現(xiàn)“人類歷史的‘還原’”和“文化原理的還原”。張藝謀的電影采用民俗文化的方式傳達(dá)了民俗風(fēng)格和民族個性,使張藝謀的電影帶著人類學(xué)和民族志的特性,而民族志是了解一個民族一個地區(qū)的一種基本資料。本文從形式層面上對張藝謀電影進(jìn)行人類學(xué)研究,通過對張藝謀電影的研究發(fā)現(xiàn)張藝謀的電影從四個方面實(shí)現(xiàn)了影片的人類學(xué)特色。
首先是影片的空間、造型:張藝謀的電影的空間、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華民族民族風(fēng)情的豐富體現(xiàn),電影里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的風(fēng)貌,如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所展現(xiàn)的中國古代的特殊居住方式――封閉的四合院,還有那沒有理由的封建的生活制度和習(xí)俗等等,這些都是張藝謀的影片從空間和造型上給予的視野,是人類學(xué)者們對中國社會生活研究的真實(shí)方便的素材。
其次是色彩運(yùn)用:色彩是電影表現(xiàn)象征作用的的一個主要媒介,色彩也是一個國家精神靈魂得以闡釋的對象。“紅色有其共通性,紅色代表革命。中國五千年文化中,在傳統(tǒng)意念上,紅色更多是代表熱烈,象征太陽,火熱,熱情,這亦是全人類共同的感覺。”張藝謀的影片中大量的運(yùn)用了紅色,似乎紅色以成為張藝謀和中國影片的標(biāo)志。張藝謀對紅色的運(yùn)用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他用紅色闡釋了中國及中國人結(jié)婚等生活習(xí)俗等方方面面。紅色是張藝謀自己偏愛的色彩,張藝謀愛用紅色作為自己電影的底色,張藝謀的影片中的紅色,或許對于人類學(xué)研究者來說,紅色就是中國民族的一個象征,苦難與進(jìn)步同在的象征。
再次是音樂的運(yùn)用:中國樂器和豐富的音樂形式在張藝謀的影片中大量出現(xiàn),體現(xiàn)了中國民族精神文化的音樂,張藝謀注重在電影中使用音樂符號的象征作用達(dá)到了一定的表意效果和影片表現(xiàn)力度。他所用的音樂帶著傳統(tǒng)的民俗味――老腔、秦調(diào)、皮影戲、陜北民歌等,在有點(diǎn)的時間和空間內(nèi)展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如《黃土地》中陜北信天游的歌聲,《活著》中老腔的曲調(diào)和《秋菊打官司》中秦腔的曲調(diào)等對于人類學(xué)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文獻(xiàn)意義,同時也成為其他國家研究中國人文的一個重要素材。
最后是方言的使用:張藝謀在影片中運(yùn)用的方言增強(qiáng)了民俗化和寫實(shí)化特征,《秋菊打官司》中的陜北方言,《一個都不能少》的河北方言,《千里走單騎》的云南澄江縣的澄江方言等。方言是中國文化的承載者,蘊(yùn)含著優(yōu)秀的文化底蘊(yùn),是中國文化的長久以來的精華所在,研究中國各地方言,也是認(rèn)識和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張藝謀的電影中也有涉及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方面的東西,如《千里走單騎》中,加入了“儺戲”這樣的民俗載體,吸引了大批的人類學(xué)家進(jìn)行對“儺戲”的研究。總之,張藝謀的電影中運(yùn)用的這些民族符號的實(shí)體或客體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民族的一個縮影,對于認(rèn)識中國的文化習(xí)俗和藝術(shù)形態(tài)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當(dāng)代美國人類學(xué)家S?南達(dá)在她的《文化人類學(xué)》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在研究人類變化中,人類學(xué)家壩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人類個體的人差異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群體之間的差異上。他們研究的是在生存、發(fā)展中相互依賴并擁有同一生活方式的人群社會。”從人類學(xué)研究的需求上來講,我們希望張藝謀的電影多挖掘自己國家的民俗,注重我國民俗文化元素的原型展現(xiàn),這樣的影片會更加有著歷史的厚重感,也希望張導(dǎo)演的能夠把黑澤明的藝術(shù)和民族的風(fēng)范相一致的去研究電影和藝術(shù)及社會的關(guān)系,創(chuàng)作出更優(yōu)秀的電影來。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彩性為我國藝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對于文藝創(chuàng)作者要善于從不同的視角去研究和挖掘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深刻內(nèi)涵,在實(shí)踐創(chuàng)作豐富多樣的前提下促進(jìn)藝術(shù)理論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篇5
西方人類學(xué)最初建立于一定數(shù)量的公設(shè)之上(實(shí)證主義、客觀主義、原始主義等等),這些公設(shè)在幾百年間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用于證明人類學(xué)研究社會的各種特質(zhì)(宗教的、傳統(tǒng)的等等)。針對西方中心的人類學(xué)模型的后殖民爭論,引發(fā)了對人類學(xué)知識視角、構(gòu)建模式,乃至其最近提出的“他性”認(rèn)識論本質(zhì)的重新審視。不過,非西方人類學(xué)傳統(tǒng)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表明,盡管替代性理論和研究方法得以誕生,卻未必會在這場實(shí)證主義的爭論之后出現(xiàn)一種“霸權(quán)式”的西方人類學(xué)和一種西方的“地方主義”。在這一點(diǎn)上,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案例有著特別的意義,因?yàn)樗崾玖艘环N雙重的、不一定繼承西方的殖民主義。
引子:人類學(xué)中的殖民問題
數(shù)年來,后殖民批評被大量引入“人”的科學(xué),特別是參與到對人類學(xué)知識本質(zhì)的質(zhì)疑中來。民族學(xué)家的責(zé)任問題因而被從各個方面(政治的和意識形態(tài)的)進(jìn)行無情的后殖民主義審查,不論其批評來自于之前被殖民化及“民族研究化”的國家(這種情況曾十分常見),或來自于以前的殖民者自身(現(xiàn)在越來越多)。從此,從事人類學(xué)被附上了沉重的罪孽:即自認(rèn)為是“殖民”或“霸權(quán)”性的,以至幾乎難以想像,研究者如果不或多或少地開展些人類學(xué)的自我批評,能取得什么進(jìn)步。于是,人們對西方霸權(quán)在越來越國際化的社會科學(xué)和人類學(xué)中的作用有了廣泛的爭論,而且來自于前殖民地國家(通常也是19、20世紀(jì)的民族學(xué)家經(jīng)驗(yàn)考察的地方)的聲音的出現(xiàn),則引發(fā)了一場激烈又不乏益處的討論,其對象便是這個――必須承認(rèn)――曾一度傾向于樹立或認(rèn)可某些明顯依附殖民意識形態(tài)假設(shè)的觀念(如原始主義)的學(xué)科。
后殖民主義思潮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從事民族學(xué)工作的政治條件,并考慮政治是如何作為背景組織起其知識的,不論是在研究本身的層面(民族學(xué)者在田野和受訪者互動的方式,Ghasarian,1997),還是在選擇概念以解釋現(xiàn)象的層面。
人們將永無休止地強(qiáng)調(diào),正是某些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基石鑄造了西方認(rèn)識他者的歷史,因此也鑄造了民族學(xué)或人類學(xué),指引其工作和范式的發(fā)展方向,特別是在19世紀(jì)的歐洲,當(dāng)其誕生成為一門專門學(xué)科時(Kilani,1992)。然而,攻擊殖民主義太過容易:其范圍含糊不清。作為范疇,又籠統(tǒng)地包括了某些人對他者歷史的權(quán)威發(fā)聲、被控制的政治單位、強(qiáng)加社會和智識模型等。殖民主義這一提法涵蓋了太多內(nèi)容,――但是其核心問題都是統(tǒng)治。如果說人們認(rèn)可針對以上元素的批評的重要性,因?yàn)樗鼈兊拇_在科學(xué)知識中產(chǎn)生了回響,那么作為人類學(xué)家,我仍認(rèn)為沒有必要僅僅是為了不受懷疑而任由一個問題過多地占據(jù)我們――正如后現(xiàn)代主義曾做的那樣。
圍繞著后殖民主義的問題最終將一步步把(西方)民族學(xué)者拖向某種永久的自我鞭撻,仿佛他們曾是西方殖民計(jì)劃的活躍人,理應(yīng)擔(dān)負(fù)起前人(沉重的)罪孽負(fù)荷(Bruekner,1983),而且仿佛地球上的所有社會都從根本上由西方和其他世界之間的歷史關(guān)系――以意識形態(tài)、政治、經(jīng)濟(jì)的方式――界定。人類學(xué)知識從而長期遭受大量的指指點(diǎn)點(diǎn),從內(nèi)部到外部都被批評和殖民計(jì)劃相勾結(jié),而實(shí)際上,占其產(chǎn)出最低限度的法國也的確傷害了該學(xué)科的整體形象(Panoff,1977)。從滋生安格魯一撒克遜世界中的后現(xiàn)代及后殖民主義批評的米歇爾?福柯與“法國理論”開始,學(xué)界輿論就變成了一種政治輿論,旨在將科學(xué)放人政治的角斗場,以便對其進(jìn)行政治角度的考核(然而不對政治輿論做科學(xué)考核)。不過,后殖民的反思――它首先是反殖民主義的――仍存有盲角,其中之一便是地區(qū)殖民主義。后者并非一定揭示出西方帝國主義或其意識形態(tài)輪廓。本文即旨在探討此話題。
東方主義和對亞洲的民族學(xué)想象
Peter Van Der Veer和Stephan Feuchtwang最近提出,人類學(xué)應(yīng)轉(zhuǎn)向?qū)喼奚鐣难芯?兩人分別指印度和中國),這不是為了衡量列維一斯特勞斯和路易?杜蒙的比較主義所珍愛的人類社會的“重大差異”(列維一斯特勞斯,1958;杜蒙,1964),而更多地是為了在視角改換的框架之下,批評人類學(xué)所關(guān)注的本質(zhì):自我指向的西方人類學(xué)矛盾地將其合法性建立在“我們談?wù)撍撸缤覀兙褪撬摺边@一觀念之上,然而當(dāng)?shù)氐纳鐣幕蛩夭坏芤饘ξ鞣侥P偷男抻?Van Der Veer,2009;Feuehtwang,2009),甚至是對視角的修訂――這正是我們討論的出發(fā)點(diǎn)。尤其是,在西方和“剩余世界”的“大分享”框架之下,――Jack Goody曾呼吁其在建構(gòu)認(rèn)知模式中的重要性――亞洲社會占據(jù)了獨(dú)特地位:相對于研究非洲或大洋洲的人類學(xué)而言,研究亞洲社會的(西方)人類學(xué)是學(xué)科中最為落后的一分子;但是如同非洲和大洋洲被同樣標(biāo)上想象中的原始主義標(biāo)簽一樣,亞洲則被標(biāo)上一份特別的他性標(biāo)簽――即東方主義。即便在內(nèi)心深處不愿意承認(rèn),民族學(xué)者在建立亞洲的形象過程中仍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其首要便是將其封人一個建立于中東這樣的熔爐的、寬泛的“東方”范疇。在這一視角下,愛德華?薩義德緊跟米歇爾?福柯和雅克?德里達(dá)之后,從西方把東方描繪成幻想之鏡,以借助其建立文明和地理認(rèn)同出發(fā),對西方范疇進(jìn)行了解構(gòu)(薩義德,1978)。
人類學(xué)知識及其矛盾的爭論:殖民主義和“雙重殖民主義”
亞洲尤其提供了(社會一政治和民族志式的,但也是科學(xué)的)一些地點(diǎn),在那里,西方的殖民思想以及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被以不同方式解讀。圍繞殖民化及去殖民化的問題,數(shù)年來已經(jīng)毫不夸張地對人類學(xué)討論進(jìn)行了(請?jiān)试S我玩?zhèn)€小小的字眼游戲)
“殖民”,以致于人們有時把相對獨(dú)立的后殖民研究跟當(dāng)代的批評人類學(xué)搞混。而這些完全屬于政治性質(zhì)的爭論背景,則顯現(xiàn)出認(rèn)識論模式之間的對立:功能主義和釋經(jīng)學(xué)(是基于功能的模型還是基于意義的模型),現(xiàn)實(shí)主義描述(即宣稱民族學(xué)家應(yīng)“如實(shí)”描寫社會和文化現(xiàn)實(shí))和文本建構(gòu)主義(即相反地認(rèn)為民族志是對他者的敘事建構(gòu)),古典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
通常,西方人類學(xué)家(特別是北美人類學(xué)家)會宣告實(shí)證主義和人類學(xué)中的簡單二分法已經(jīng)終結(jié)(例如像他們一我們,北部一南部,西方一東方等)。但實(shí)證主義仍有其吸引力:只需舉出像“自然主義”傾向(神經(jīng)生物學(xué)和認(rèn)知學(xué))和相對的“文化主義”傾向(文本和翻譯的范式)之間的沖突,便可理解19世紀(jì)時、將社會科學(xué)和人文分隔出來的古老對立(研究自然的科學(xué)vs研究精神的科學(xué))(Oba-dia,2007)。人類學(xué)中后現(xiàn)代主義和文化研究的捍衛(wèi)者們傾向于譴責(zé)“自然主義者”固守科學(xué)主義的姿態(tài)且企圖重拾實(shí)證主義的視角,而實(shí)證主義者們則相應(yīng)地批評這些文化主義的“文本至上”的人類學(xué)家。
這場論戰(zhàn),其各自的論點(diǎn)、得失和理由都很復(fù)雜,在此不能一一敘述,但要牢記它引起了西方當(dāng)代人類學(xué)的極大動蕩和分裂,而實(shí)證主義則成為劃分這兩種趨勢的分界線。但是,實(shí)證主義卻是不容易被察覺的:它可能藏在認(rèn)知的“外省”,特別是在社會科學(xué)在整個20世紀(jì)(尤其是后半葉)走向國際化、 傳播到西方以外的過程中,為曾是人類學(xué)的簡單“田野”或“對象”的社會所采納和改革。
人類學(xué)知識的“地方主義”概念是在文化研究和底層研究的框架下形成的,它具有重大的啟發(fā)意義,不是為了簡單地更進(jìn)一步,而是為了轉(zhuǎn)移。如果將關(guān)注的相互性推到底,那么面對西方在知識上的霸權(quán)位置(不論是歷史學(xué)、社會學(xué)、人類學(xué)……),作為最典型的研究他性的科學(xué)――人類學(xué),首當(dāng)其沖需要一場認(rèn)識論的轉(zhuǎn)變。首先,它得向眾多的(西方和非西方的)聲音開放智識討論,允許其表達(dá),并且它為研究這些曾被殖民、剛成為人類學(xué)的新聲如何“在別處”表達(dá)“別處”提供了可能。在此意義上,
“地方”的提法至關(guān)重要:因?yàn)椴坏切┏1诲e誤以為是普適的人類學(xué)理論依賴于其形成的文化和社會形態(tài)(Lederman,1998),且同樣的人類學(xué)知識也會被不同的話題所“地方化”(知識的意識形態(tài)或認(rèn)識論地區(qū):結(jié)構(gòu)主義、社會學(xué)主義、心理分析主義……)。跟這種雙重地方主義相對應(yīng)的是一種雙重殖民主義:政治(和經(jīng)濟(jì))上的殖民主義以及科學(xué)的殖民主義,兩者在尼泊爾的案例中造成的影響和激起的反抗不盡相同。這就是我們從尼泊爾人類學(xué)的最近歷史中所學(xué)到的。
人類學(xué)在尼泊爾的發(fā)展
首先,尼泊爾人類學(xué)不是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前者把尼泊爾社會當(dāng)作研究對象,長期為在尼泊爾工作的外國人類學(xué)家所統(tǒng)治;后者和前者的對象一致,但是由本土的研究者實(shí)行。針對那些對尼泊爾影響巨大的國家在經(jīng)濟(jì)、政治和智識上的殖民主義的斗爭,獨(dú)特地沒有采取我們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形式――讓這些前“原始人”或“當(dāng)?shù)厝恕边M(jìn)入大學(xué)。不過,亞洲卻成為了人類學(xué)知識的后殖民爭論的一個特別活躍的熔爐。
其中,在印度尤其誕生了數(shù)個在人類學(xué)知識去西方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潮。雖然早期的印度式“比較社會學(xué)”是由歐洲學(xué)者建立的(路易?杜蒙和David Pocock):Homi Bhaba,Gayatri Spivak和人類學(xué)家Ajrlln Appadurai都是知識分子的領(lǐng)軍人物。同樣,在印度繁榮起來的底層研究,其最初的使命是批評由“殖民者”所書寫的南亞社會史,之后才廣泛傳播到原涉及的地緣政治地區(qū)之外(Poucheo-adass,2000)。從此,(幾乎)全體人類學(xué)都遭到了這一批評,后者被引向外界且由文學(xué)所引發(fā),在被人類學(xué)所消化后,人們將其稱成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
盡管如此,在西方成形的“后殖民”論戰(zhàn)仍保留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痕跡:它讓歐洲和美國學(xué)者永無休止地反思和批評自我的過錯,以至于他們把這一本來是談?wù)撐幕娜祟悓W(xué)項(xiàng)目單獨(dú)分解出來,轉(zhuǎn)變?yōu)橐豁?xiàng)自戀的(談?wù)撁褡鍖W(xué)者的)項(xiàng)目(Ghasarian,1997);另外,它還鋪展成一系列只和西方有關(guān)的爭論――以至于爭論的聲音奇怪地都帶有西方口音,即便它們來自于南方。不是所有亞洲國家都是印度,而且這種“后”尤其是“反”殖民的關(guān)系仿佛不以同樣方式影響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社會,盡管它們都是人類學(xué)研究的對象。尼泊爾就是這樣:如果人們考慮到人類學(xué)家的數(shù)量和總?cè)丝诘谋嚷剩抢锏娜祟悓W(xué)是世界上最為發(fā)達(dá)的。在這個面積約147000平方公里、擁有2500萬人口和數(shù)十個被登記的族群的國家,幾乎沒有地區(qū)或者族群不被當(dāng)成為民族志調(diào)查的對象。在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或者更應(yīng)該說那些人類學(xué),現(xiàn)在主要是針對同一亞洲國家的數(shù)種西方人類學(xué)。但是近30年來,一種尼泊爾的(也就是本土的)人類學(xué)的出現(xiàn),催生了一種既獨(dú)立又基于外來模型形成的、奇特的智識傳統(tǒng)。
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的出現(xiàn)
尼泊爾人類學(xué)實(shí)際上先是研究一個亞洲國家的西方人類學(xué)。她起步于Christoph Von Ftirer-Haimen-doff對北部山脈的夏爾巴人的研究(Ftirer-Haimendorf,1964):從此,尼泊爾成為地球上被探索得最為徹底的民族志田野之一,以至于根據(jù)著名的Hopi人的諺語,一個尼泊爾家庭由父親、母親、孩子、狗以及一個人類學(xué)家組成(Luger,2000)。尼泊爾靠著它混雜的民族和宗教特色、巨大的文化豐富性、還有――必須承認(rèn)――美麗的自然環(huán)境及在一個擁有如此好客的居民的國家里從事田野工作的便利性,成為越來越年輕的西方民族學(xué)者的理想田野工作地點(diǎn)。對于當(dāng)?shù)匮芯空邅碚f也是如此,盡管其學(xué)術(shù)配置遠(yuǎn)遠(yuǎn)不如西方。正如Krishna Hachhetu所指出的,“尼泊爾的社會科學(xué)長期為政府和社會所忽視”(2002:3640),他指出,該國自20世紀(jì)50年代向市場經(jīng)濟(jì)和國際貿(mào)易開放以來,主要投資在技術(shù)性科學(xué)方面。
然而,尼泊爾人類學(xué)(以及社會學(xué))仍成功地為自己清理出一條道路,從而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研究人和社會的重要角色之一。當(dāng)然,(在研究組織上)按國際標(biāo)準(zhǔn)建立起來的當(dāng)?shù)匮芯繖C(jī)構(gòu)從1970年代以來在人類學(xué)知識的學(xué)習(xí)和建制上取得了突飛猛進(jìn)的進(jìn)步。首先,Tribhuvan大學(xué)一直是社會科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和科學(xué)發(fā)動機(jī)。自1973年創(chuàng)立尼泊爾和亞洲研究所,1981年在Tribhuvan大學(xué)建立人類學(xué)和社會學(xué)系,以及1985年成立尼泊爾社會學(xué)和人類學(xué)會以來,大型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不間斷地在其上升過程中舉行(1992年的尼泊爾人類學(xué):人民,問題和過程;1997年的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與社會學(xué):文化、社會、生態(tài)和發(fā)展)(更多細(xì)節(jié)參見Battachan,1987)。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從一開始便依賴來自于印度和西方的雙重影響,而且它必須在尼泊爾有關(guān)人的科學(xué)中獲得一席之地,后者由歷史和經(jīng)濟(jì)學(xué)所統(tǒng)治。
通過逐漸從其外國奠基者中獲得獨(dú)立,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從1980年代開始成為一門全國性的學(xué)科。但是尼泊爾還沒有――或者說暫時沒有――關(guān)于是否要普遍重塑其方向和模型的真正爭論,例如像印度人類學(xué)那樣,特別是在路易?杜蒙逝世后,對其整體論方法的批評(Assayag,1998)。突然之間,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仿佛在一種古典主義的、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由西方人從事)和一種尼泊爾式的人類學(xué)(由當(dāng)?shù)匮芯空邚氖?之間拉扯不清,直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即便兩者擁有相同的認(rèn)識論、田野方法和概念,這兩種人類學(xué)卻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家和社會學(xué)家自己也認(rèn)識到了這一點(diǎn),懷抱著強(qiáng)烈的責(zé)任感,他們在應(yīng)用研究的問題上公開地宣揚(yáng)公共政治在自然資源管理、經(jīng)濟(jì)發(fā)展、教育和衛(wèi)生領(lǐng)域的置入或便利化(Allen et al.,1994,Chhetri et Gurung,1999,Devkota,2001)。社會科學(xué)還未在大學(xué)里取得發(fā)展,便已經(jīng)在當(dāng)?shù)匕l(fā)展的項(xiàng)目框架下被教授和被應(yīng)用(在政治決策系統(tǒng)的層面,特別是pan-chayat),這一必須和社會環(huán)境條件相調(diào)和的重點(diǎn)被保留了下來:社會科學(xué)應(yīng)對何種需求和/或問題作出回應(yīng)?(Battachan,1987)
發(fā)展一種應(yīng)用的而非嚴(yán)格的學(xué)院和基礎(chǔ)人類學(xué)同樣是出于政治和經(jīng)濟(jì)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同意為其發(fā)展作出努力,但這種努力是常常變化的:社會科學(xué)通常在大學(xué)中被邊緣化,除非是在非常的政治動蕩時期(1990年代);在那種時期,人們持有期許,認(rèn)為社會科學(xué)能“產(chǎn)生”政治體系層面的忠誠公 民,而且/或者社會科學(xué)能為國家提供可支配的、關(guān)于社會資源的信息,從而為國家發(fā)展作出貢獻(xiàn)(Hachhetu,2002)。尼泊爾發(fā)展自己人類學(xué)的努力過程顯現(xiàn)出了某種民族自豪感。從而,當(dāng)?shù)厮M(jìn)行的人類學(xué)工作無論是否和國際合作,都表現(xiàn)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應(yīng)用人類學(xué)傾向(Bista,1987:7),后者必須并行參與到“民族文化和公民身份推廣”上來(同上)。另一方面,學(xué)院框架出現(xiàn)問題時,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也借助于其他的贊助和支持,特別是來自于非政府組織或個人的資助,后者常能提供比大學(xué)好得多的資金和研究條件(Hachhetu,2002:3638)。
殖民主義的問題以及videshi人類學(xué)的批評
因?yàn)樯鲜鲈颞D―這還要加上尼泊爾擁有其自豪的、沒有殖民時期的歷史,盡管有近處(印度)和遠(yuǎn)處(英國)鄰居的多次嘗試――在許多非西方人類學(xué)中被提出的殖民主義問題,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被擺在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面前。如果說殖民主義在歷史和國際上都確實(shí)存在,那么這個國家從1950年代初開始,的確處于一種對其他國家的經(jīng)濟(jì)以及某種程度的智識依賴的關(guān)系中。不過,有關(guān)尼泊爾,的確有一份非常古老的民族志(可追溯到18世紀(jì)),其描述跟內(nèi)容都清楚地揭示了其暗含的殖民計(jì)劃(Beine,1998)。因?yàn)楫?dāng)人們提到殖民主義的時候,常常會忘記內(nèi)部殖民主義的存在,而對后者的分析揭示出一種人類學(xué)認(rèn)知的政治社會學(xué)。在該背景下,針對videshi(即外國人)人類學(xué)導(dǎo)向的批評最終推動了本土人類學(xué)的自治運(yùn)動。前者可歸納為以下幾點(diǎn):
――很少在尼泊爾傳播其工作內(nèi)容(其出版的受眾是國際化的);
――拒絕運(yùn)用人類學(xué)知識為發(fā)展規(guī)劃服務(wù):
――相對于占絕大多數(shù)的印歐人口,更多地只對占少數(shù)的藏緬族群(bothia)感興趣(Chhetri和Gurung,1999);
――對涉及非政府組織的行為或發(fā)展過程中的社會經(jīng)濟(jì)變化的變量不感興趣。
總而言之,這是一種在尼泊爾而非為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另外,它重拾了某些研究“遙遠(yuǎn)”和“奇特”民族的人類學(xué)傾向:對尼泊爾人民做的民族志時常依附于這種浪漫主義的傾向(后者在西方人類學(xué)中歷史久遠(yuǎn)),即把他們當(dāng)作是未經(jīng)探索的遠(yuǎn)方國度的居民,保存了某種形式的文化真實(shí)性(Beine,1998)。正是面對這種基于地緣文化的遙遠(yuǎn)建構(gòu)人類學(xué)知識的沉重趨勢,人們需要尼泊爾式的尼泊爾人類學(xué)。正如加德滿都最早的人類學(xué)教授之一Dor Bahadur Bista合理宣稱的:“在尼泊爾,傳統(tǒng)在生活中至高無上;但諷刺的是,對于社會學(xué)和人類學(xué),我們完全沒有用來遵循的傳統(tǒng),只有用來建立傳統(tǒng)的傳統(tǒng)。”(Bista,1987:6)“傳統(tǒng)”一詞所指的更多的是一個思想學(xué)派,而不僅是一個學(xué)院機(jī)構(gòu)。而且對于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來說,與印度和歐洲先輩(部分地,但必要地)割斷世代聯(lián)系、重新創(chuàng)立,這既是難題,也是機(jī)會。
然而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已然開始描繪王國內(nèi)部的殖民主義的輪廓,探索印度教被樹立為國教以來,司法、政治、文化和語言框架的歷史發(fā)展,以及后者如何影響尼泊爾公民身份和(被指定的)種姓、(爭取來的)民族認(rèn)同之間的張力(Pradhan,2002);并且,在此意義上,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從未明顯地從西方殖民問題上汲取靈感,而是完全集中在地方殖民問題(如印度教)上。這是一場方興未艾的、針對國家的印度教的批評,后者作為一個中央集權(quán)體系,在文化、宗教和族別上統(tǒng)治著少數(shù)族群(比如佛教),將它們包納其中(Pradhan,2002)。若不經(jīng)此批評,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便面臨成為統(tǒng)治種姓和印度教傳統(tǒng)研究被統(tǒng)治和低等種姓的人類學(xué)的危險(xiǎn),其基礎(chǔ)是平原的印度教“文明”和山地的佛教“部落”――當(dāng)?shù)亍俺趺瘛报D―之間的對立。
所以說,在尼泊爾的尼泊爾人類學(xué)所采取的發(fā)展方向有兩條主要脈絡(luò):一方面,自身的發(fā)展和理論關(guān)注(內(nèi)在),另一方面,對西方人類學(xué)知識進(jìn)行本土化的模式和過程(外來)。而這一本土化遠(yuǎn)非一種人類學(xué)輸入的“被動”涵化形式:它旨在將學(xué)科真正地“尼泊爾化”(Nepalization)(Devokta,2011:34)以超越理論和分析模型的歐洲或美洲中心主義,還要摒除從事人類學(xué)過程中所暗含的文化浪漫主義。不過,從另一方面,對利于發(fā)展和政治機(jī)構(gòu)的、工具化的民族志的強(qiáng)調(diào),有把利益和角色完全和簡單分開的巨大風(fēng)險(xiǎn)。正是在這兩種趨勢的交界處,反對者們組建起一個各種智識傳統(tǒng)相互遭遇的場所,這些傳統(tǒng)帶著不同的挑戰(zhàn)參與到同一個人類學(xué)項(xiàng)目來,而它們的研究方法也根據(jù)不同的研究對象而分化:單一文化和多種文化。
文化主義的持久性
西方國家的人類學(xué)(歐洲、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均已宣告埋葬了文化主義或至少是某種形式的文化主義(本質(zhì)主義),而尼泊爾式人類學(xué)則相反地趨向于采納文化和各種民族特色文化的概念。固然,最初一批由西方學(xué)者(Furer-Haimendorf,Hitchcock等)寫成的專著帶有Franz Boas的文化主義色彩(Beine,1998),后者對做“部落”民族志即把社會和文化群體作為獨(dú)立個體相互區(qū)分的方式造成了廣泛的影響(Gautam和Thapa-Magar,1994)。還有,從亞洲社會特別是印度發(fā)出的后殖民主義批評卻矛盾地和令人不快地傾向于產(chǎn)出它們所反對的東西:一種本質(zhì)主義的身份認(rèn)同,用以對抗西方的、同樣被固化的身份認(rèn)同(Amselle,2008)。
但是,普遍的喜馬拉雅地區(qū)人類學(xué)以及特殊的尼泊爾人類學(xué),都通過眾多工作對解構(gòu)文化本質(zhì)主義和深層的族別主義作出了貢獻(xiàn)――尼泊爾人類學(xué)的領(lǐng)銜人物David Gellner的研究對這一方法作出了特別有意義的展示,即提供有說服力的替代分析理論:相對于無所不包、決定論式的“文化”概念,應(yīng)該選擇采用“性”(agency)的研究方法,重新組織自身、社會以及歷史之間的關(guān)系(Self,Society and History)(Gellner,Pfaff-Gzarnecka,Whelpton,1997)。亞洲社會曾是各種族別理論的醞釀和形成之地,后者帶來了一場對文化概念的完全修訂(該運(yùn)動的發(fā)起人有Michael Moermann,Edmund Leach);此外,亞洲(特別是喜馬拉雅地區(qū))對研究人的科學(xué)來說分外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這遠(yuǎn)不止是一種東方主義視角的去中心化而已。只舉一個特別有代表性的例子,Sherry Ortner或Vincanne Adams的研究都發(fā)展出了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前者用以解釋尼泊爾北部因一段結(jié)構(gòu)和整體上的政治歷史引發(fā)的宗教轉(zhuǎn)型(Ortner,1989),后者透過大眾旅游擴(kuò)張看待對族別的模仿性創(chuàng)造(Adams,1996)。還有,Sherry Ortner也曾通過一段微歷史對“現(xiàn)代化”的目的和終極論模式提出質(zhì)疑(0rtner,1998)。
針對“浪漫主義”的指控,在尼泊爾的西方民族學(xué)家不乏強(qiáng)調(diào):videshishi式的民族志文本和當(dāng)?shù)噩F(xiàn)實(shí)的抵觸的確揭示出“異國化”的一面,但是作為范疇(被投射在西方身上)的浪漫主義也同樣可以 回敬給尼泊爾研究者用做視角出發(fā)點(diǎn)的“發(fā)展”模型,后者既不中立也不客觀(Fischer,1987)。同樣地,和尼泊爾盛行的應(yīng)用式和發(fā)展主義專著傾向相并行的,是一種將文化作為geist或文化的“精神”重新置入分析核心的民族志:例如Dor Bahadur Bista曾經(jīng)將尼泊爾對發(fā)展規(guī)劃的反抗解釋為主要(但非全部)和印度教的宗教觀念有關(guān),特別是面對社會變遷的種種可能,產(chǎn)生一種“宿命論”思想的種姓制度(varna-iati)(Bista,1994)。除了這些最為人知的尼泊爾人類學(xué)家的工作,還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志作品同樣在這一“應(yīng)用”的方法框架下完成,試圖通過地方文化的各種形式解釋社會一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落后原因。
回到悖論
社會科學(xué),特別是人類學(xué)的國際化,究竟是學(xué)院傳統(tǒng)的標(biāo)準(zhǔn)化過程之一,還是相反地促成了特殊傳統(tǒng)的涌現(xiàn)?以上介紹的尼泊爾人類學(xué)案例讓我們得以將思路放寬到這兩種可能之外:尼泊爾人類學(xué)同時是全球化力量和當(dāng)?shù)夭┺牡慕Y(jié)果,既在面對其西方先輩時試圖模仿,又追求自我的成熟。有趣的是,在選擇“轉(zhuǎn)向應(yīng)用”時,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似乎“卡”在了Roger Bastide 40年前提出、后來被大量追述的一種可疑關(guān)系之中,即人類學(xué)作為工具服務(wù)于發(fā)展規(guī)劃。顯然,在這一導(dǎo)向中,人類學(xué)和當(dāng)?shù)匚幕⑸鐣軜?gòu)的關(guān)系被重新闡釋,人類學(xué)家的工作和挑戰(zhàn)根據(jù)社會和經(jīng)濟(jì)目的而被重新塑造――這些目的是由尼泊爾進(jìn)入世界經(jīng)濟(jì)市場,向大型西方組織的經(jīng)濟(jì)、社會、衛(wèi)生和發(fā)展標(biāo)準(zhǔn)看齊而決定的(Obadia,2006)。
在尼泊爾的尼泊爾式人類學(xué)存在一個令人驚訝的悖論,即殖民主義的循環(huán):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遠(yuǎn)離其原型、西方人類學(xué)(并且曾一度猶豫是否依附同樣屬于西方后裔的印度人類學(xué),參見Battaehan,1987),結(jié)果又回到了西方人類學(xué),并且只保留了其中最實(shí)證主義的部分――這恰恰是西方人類學(xué)在帶著批評意識審視殖民問題時已經(jīng)清除了的。在此意義上,人類學(xué)知識到處且永久受到科學(xué)主義和文化主義的誘惑,它在普適主義和相對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在歐洲和北美傳統(tǒng)中,它首先將其“非科學(xué)”的元素肅清,繼而以主觀性、直覺或感情的形式將之重新納入;而尼泊爾的人類學(xué)在受到西方后殖民主義人類學(xué)的孕育后,則(再一次)來到了這一殖民時代的科學(xué)理想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