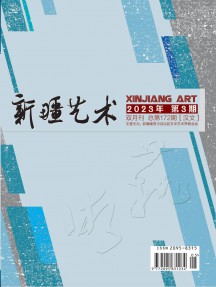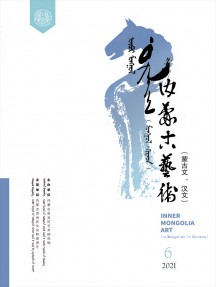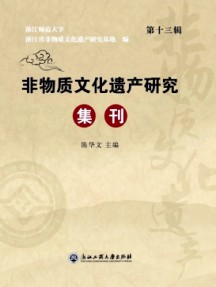非遺文化的概念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間:2023-10-11 17:26:16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非遺文化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關(guān)鍵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概念,特點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9-0218-01
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概念
什么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進(jìn)入21世紀(jì),一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新名詞闖入了國人的腦袋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這一概念出自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官方中文本。從表面上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一個偏正結(jié)構(gòu)的名詞,分為“非物質(zhì)”和“文化遺產(chǎn)”兩個部。按照一般的理解,“非物質(zhì)”是對物質(zhì)全稱的否定。就此而言,“物質(zhì)”的反義詞就應(yīng)當(dāng)是“精神”,而不是“非物質(zhì)。固然我們認(rèn)為:所謂非物質(zhì)文化就是精神文化。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非物質(zhì)文化”并非原生性的漢語概念,它產(chǎn)生于漢語語境之外。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定義作了解讀,但在不同程度上還存在著缺失,必要的時候可能會對其進(jìn)行一定的修正。
物質(zhì)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tài)是靠物質(zhì)有形文化來傳承的。表現(xiàn)為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及勞動者生產(chǎn)技能和知識觀念,它是人類物質(zhì)基礎(chǔ)和生活環(huán)境,能夠便于觀察相對固定統(tǒng)一的文化。如山川河流、樓閣庭院、生產(chǎn)機械等。非物質(zhì)文化作為一個民族維系生存最重要的精神形態(tài)則是動態(tài)無形的,流傳著的。如人的本身是物質(zhì)的,而每個人的不同形象、性格、脾氣、語言和行為的“描述”則是”’非物質(zhì)”的了。由此認(rèn)為,對非物質(zhì)文化認(rèn)識過程是一個漸進(jìn)的過程,當(dāng)然角度的不同,認(rèn)識的觀念也不同。于是,關(guān)于“文化”幾乎每一位學(xué)者都有自己的認(rèn)識和標(biāo)準(zhǔn),所有學(xué)科都定義過“文化”,事實上從未被統(tǒng)一過。最終世界文化組織把“文化”收集成兩種:一種是物質(zhì)文化,另一種是非物質(zhì)文化。把非物質(zhì)文化按照當(dāng)今的觀念和理論規(guī)定為五大類::一是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媒介語言口述的類別;二是表演藝術(shù),包括戲劇小品、舞蹈等;三是社會風(fēng)俗、禮儀節(jié)慶(定期或不定期地開展活動);四是有關(guān)宇宙和自然界知識實踐(認(rèn)識自然的過程);五是傳統(tǒng)的手工藝生產(chǎn)過程(手工作坊和傳承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都是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保護(hù)和探討它的存在和發(fā)展具有深刻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
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特點
(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性。所謂傳承性,是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具有被人類以群體或個體方式一代接一代享用、繼承和發(fā)展的性質(zhì)。如我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即:指南針、火藥、造紙和印刷術(shù)。它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象征和汗水的結(jié)晶,并在長期生活實踐中流傳下來的技藝。我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擁有豐富多彩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我們在調(diào)查時,首先要弄清這項技藝是不是我們的祖宗留下來的。這是判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
(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口頭性。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主要流傳于農(nóng)村,有的傳承人是文盲,不可能將自己所掌握的技藝和習(xí)俗整理成書,在傳承形式上主要靠口傳心授、言傳身教,再加上在傳承中有許多規(guī)矩,如“傳男不傳女”、“傳內(nèi)不傳外”等。有許多技藝屬于獨門絕技,往往隨著傳承人的離世而絕藝。再說,我國的許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往往還打上了“仙人和神秘”的烙印,甚至讓人“望而生畏”,這些技藝往往都是一脈相傳,一旦師傅過世后,這些技藝隨之失傳。故此我們要充分認(rèn)識搶救和保護(hù)這些文化遺產(chǎn)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可塑性。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口頭的傳承性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可塑性的必然。也就是說有“非遺”口頭的傳承性就有“非遺”的可塑性。特別是在“非遺”的口頭傳說、表演藝術(shù)、風(fēng)俗禮儀、節(jié)日慶典、傳統(tǒng)工藝等遺產(chǎn)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由于它的文化內(nèi)涵是通過人的活動表演來傳達(dá)給受眾的,因此在傳承傳播的過程中,將會有所變異和創(chuàng)新。如武術(shù)中的太極拳,從陳氏到楊氏,再到吳氏,還有流傳著的太極拳的八十八式等,在逐漸完善的過程中,他們還會根據(jù)不同人的特點不斷創(chuàng)新,絕不是一成不變的。
篇2
關(guān)鍵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概念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3-0104-02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現(xiàn)今社會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可以說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人類文明的一種集中體現(xiàn)方式,因此保護(hù)“非遺”是對人類的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功在千秋的保護(hù)。根據(jù)聯(lián)合國《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下簡稱《公約》)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定義:“‘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指被各社區(qū)群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xiàn)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guān)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根據(jù)我國2011年頒布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第2條的規(guī)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以及與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相關(guān)的實物和場所。”這兩個法律文件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概念界定如出一轍,現(xiàn)階段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概念也沒有太多理論上的爭論,因此本文中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概念就采用了我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中的定義。
根據(j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對“非遺”的定義,可以看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存在于全人類發(fā)展進(jìn)程中的必然產(chǎn)物,我們看到的很多“非遺”內(nèi)容可能是以依賴一種物質(zhì)來表現(xiàn)或一定物質(zhì)形式表現(xiàn)出來,比如一種音樂的演奏樂器,一項技藝的制作成果。但是,那只是它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而實質(zhì)重要的是傳承人所掌握的文化本身,它是不能像物質(zhì)一樣脫離人類自身獨立存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一定始終與人類特定群體的生活、生產(chǎn)精密聯(lián)系,并逐步形成。早在2007年,我國的第二個“文化遺產(chǎn)日”活動會展期間,總理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做過意義深遠(yuǎn)的闡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都是幾百年、幾千年傳下來的,為什么能傳下來,千古不絕?就在于有靈魂,有精神。一脈文心傳萬代,千古不絕是真魂。文脈就是一個民族的魂脈。今天,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就是傳承民族文化的文脈。”總理所指的“文脈”在筆者看來,就是一種人類的創(chuàng)新形式,是一種全民族的世代傳承,要使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蓬勃的傳承下去,使“文脈”能繼續(xù)有力地跳動,而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人正是這個“文脈”延續(xù)的必然要件,所以說,我們要重視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人的基礎(chǔ)作用,要切實加強對傳承人關(guān)心與支持。
一般認(rèn)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個體傳承人傳承,如口頭文學(xué)、表演藝術(shù)、手工技藝、民間知識類的民俗文化等;二是群體傳承,如婚慶禮儀、民間節(jié)日等民俗活動,一般屬于民眾集體共享并依循,為民眾集體擁有,也需要民眾集體的世代傳承。可以想象在前一種形式中,個體傳承人是“非遺”的重要傳遞者和承載者,最初的始創(chuàng)者用自己的辛勞汗水與智慧結(jié)晶,創(chuàng)造了“非遺”的精湛的技藝和文化傳統(tǒng),在此基礎(chǔ)上他們又世世代代承載著“非遺”,使得我們現(xiàn)代人能繼續(xù)保有豐富多彩的文化成果。傳承人在對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那么如何界定“傳承人”的范疇,同時“傳承人”又有何權(quán)利與義務(wù)?當(dāng)前學(xué)界大致存在以下兩種觀點。
黃玉燁先生認(rèn)為“出于保護(hù)國家重大利益的需要,國家還可以依法公開宣稱自己是某項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傳承人。”田文英先生則認(rèn)為“那些進(jìn)入公有領(lǐng)域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其傳承人和作者的權(quán)利都應(yīng)該由國家來行使。國家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主動收集本國瀕臨失傳的有價值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材料,使自己成為傳承人。”“由某個社會組織依法發(fā)掘研究并持有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該社會組織是傳承人”。顯而易見,他們主張的是:很多傳承人不明,沒有具體傳承人的內(nèi)容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第一種傳承類型的非遺,比如說:一些民間節(jié)日、傳說、禮儀風(fēng)俗、生活方式等等。這些遺產(chǎn)是根植于民族群體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是整個少數(shù)民族群體擁有的。這些非遺沒用限定于某一個具體的人或是團體的傳承人,而是靠一個族群或國家來傳承的。因此,可以將國家和族群認(rèn)定為傳承人,更有利于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另外有學(xué)者認(rèn)為,傳承人的范圍不包括國家或群體。如李磊先生認(rèn)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是指由一國群體創(chuàng)作,因此,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傳承人應(yīng)該是一些具體的公民或者單位,這些公民和單位在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傳承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國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宜將國家列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傳承人。從上述論述中,可見李磊先生認(rèn)為“國家”既不是傳承人,也無傳承之功能,更不能成為傳承主體。對此,筆者認(rèn)為,導(dǎo)致前述問題產(chǎn)生的實質(zhì)問題是他們混淆了“傳承人”和“傳承主體”兩個不同概念。前兩種觀點認(rèn)為傳承主體即等同于傳承人,所有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都能由傳承人的方式傳承。這種方式容易將群體的權(quán)利與個體的權(quán)利混淆起來,使得民眾集體都成為了傳承人,讓本應(yīng)該保護(hù)的人沒用得到切實保護(hù)。俗話說“都有等于都沒有”,如果依照前述觀點會使得“傳承人”的概念空泛化。后一種觀點,只提及了“非遺”個體傳承人的作用,而沒有確認(rèn)民眾族群和國家也是當(dāng)然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主體,只單純地認(rèn)為國家應(yīng)該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進(jìn)行保護(hù)。李磊先生所說的觀點,“國家不擁有傳承文化的作用”,筆者認(rèn)為此種觀點比較牽強。眾所周知,眾多自然人的組合才是一個國家的基礎(chǔ),這些特定的自然人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擁有共同的文化和思想,那么“國家”這個由眾多自然人組合而成的群體也是理所當(dāng)然成為非物質(zhì)文化的傳承主體。同時可見民眾族群與國家在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中起到了與生俱來的當(dāng)然作用。
綜合當(dāng)前學(xué)者們的主流觀點,筆者認(rèn)為,民眾族群和國家也是文化傳承主體,他們都有保護(hù)、弘揚和傳承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責(zé)任,當(dāng)本國家或民眾族群自身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受到侵害之時,他們亦能行使維護(hù)正當(dāng)利益的權(quán)利。盡管,現(xiàn)階段并沒有立法,但在法理上這是可行的。可借鑒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沒有具體個人傳承的情況下,由族群或者國家成立一個特定機構(gòu)來負(fù)責(zé)管理,并且可以授權(quán)使用其所管理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同時收取一定費用,用于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和振興,或者當(dāng)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被侵犯之時,可以代表受侵犯的相關(guān)方面去采取合理的方式去維護(hù)權(quán)益。傳承主體在理論上包涵著傳承人,很多人可能共享或者共同掌握著某一種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非遺”也可能有很多傳承主體,但并不是所有傳承主體都能成為傳承人,只有當(dāng)符合相應(yīng)必要條件時,才能成為合法的真正意義上的傳承人。
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中沒有明確定義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而是規(guī)定了成為傳承人的條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yīng)當(dāng)符合下列條件:(一)熟練掌握其傳承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二)在特定領(lǐng)域內(nèi)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區(qū)域內(nèi)具有較大影響;(三)積極開展傳承活動。”對于這三個條件,應(yīng)該是要求同時具備,才能成為所謂傳承人。同時,回顧一下在200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保護(hù)法》(草案)中,規(guī)定了單位或團體可以作為傳承人。但是,在2011年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中并沒有采用團體、單位傳承人這樣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傳承人是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同時是針對可以由個體傳承的“非遺”所設(shè)置的。傳承人應(yīng)該是指個體,而不能是國家或者團體。我國著名的民族學(xué)家祁慶富教授對“傳承和傳承人”的學(xué)術(shù)史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與分析,把“傳承人”的概念定義為:“在有重要價值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過程中,代表某項遺產(chǎn)深厚的民族民間文化傳統(tǒng),掌握杰出的技術(shù)、技藝、技能,為社區(qū)、群體、族群所公認(rèn)的有影響力的人物。”筆者梳理了各家觀點,并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對傳承人的要求的基礎(chǔ)上,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定義為:能熟練掌握國家或地方政府認(rèn)定的各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并在本領(lǐng)域內(nèi)有較大影響力,為公眾所認(rèn)同,并能積極開展傳承活動的個體。其特征具體如下。
第一,能熟練掌握國家或地方政府認(rèn)定的各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個體傳承人作為某項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的實際掌握者,必須是通過國家或者相應(yīng)地方主管部門的認(rèn)定并且許可。這是作為個體傳承人的合法基礎(chǔ)。
第二,該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在本領(lǐng)域內(nèi)有較大影響力。對于傳承人所掌握的“非遺”項目,不能簡單歸結(jié)為掌握某種技藝或者某種特長,需要實際扎根于某個特定領(lǐng)域內(nèi),并且能夠形成較大的影響力,從而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典范。
第三,該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需為公眾認(rèn)同并能積極傳承。傳統(tǒng)文化豐富多彩,良莠不齊,這里定義的“非遺”項目必須是健康積極,并能為民眾集體喜聞樂見,并能使得世代傳承的文化成果。
非物質(zhì)文化作為社會文明的集中表現(xiàn)形式,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不僅是個體傳承人還是民眾族群與國家都是傳承文明的使者,我們要始終如一予以重視,為他們創(chuàng)造更好的工作與生存環(huán)境,以期更好地將非物質(zhì)文化繼續(xù)傳承并發(fā)揚光大。
參考文獻(xiàn):
[1]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hù)工程國家中心.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hù)工程普查工作手冊[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5.
[2]李斌.我國第二個“文化遺產(chǎn)日”之際、李長春參觀中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專題展[N].人民日報,2007-06-10.
[3]黃玉燁.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法律保護(hù)[M].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08.
[4]田文英.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傳承人的法律地位[N].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報,2002-07-05.
篇3
1 河南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的特點及價值
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具有獨特性、流變性、傳承性、綜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豐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態(tài)的口頭性,表現(xiàn)在地方戲曲、民間文學(xué)、曲藝、民歌、語言文字習(xí)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墜子、豫劇、各地方言中的諺語、歌謠、神話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具有深刻的“廣泛性”。如河南的豫劇,其獨特的旋律與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類方言語音、詞匯的廣泛運用,唱詞、念白等多具有口頭表達(dá)性,使其在文藝表現(xiàn)上更具地方特色。
從河南省第一批非遺文化名錄來看,涉及語言文學(xué)類的就有18項。如虞城縣花木蘭傳說、汝南縣梁祝傳說、泌陽縣盤古神話、武陟縣、西平縣、汝南縣、平輿縣等關(guān)于董永與七仙女的傳說,還有輝縣市的張生與崔鶯鶯的故事、衛(wèi)輝市關(guān)于柳毅的傳說,濟源市關(guān)于邵原創(chuàng)世的神話等,都具有獨特的文化歷史價值。除此之外,南陽市的牛郎與織女的傳說、靈寶市關(guān)于皇帝的傳說、長葛市關(guān)于葛天氏的傳說、濮陽縣關(guān)于帝舜的傳說等等,這些民間文化不僅對現(xiàn)代人民的思想意識產(chǎn)生影響,也蘊涵了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價值,尤其是在歷史學(xué)、語言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審美等領(lǐng)域,體現(xiàn)了民族精神。在語言文化類非遺文化中,方言占據(jù)重要地位。如豫劇、河南墜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礎(chǔ)上。
2 河南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檔案管理現(xiàn)狀及問題分析
河南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的收集、整理、鑒定、確認(rèn)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豐富的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仍有待進(jìn)一步挖掘,尤其是從以方言為特征的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對口頭文學(xué)、民間文學(xué)類文化形式進(jìn)行多方面記錄和歸類管理,以便于繼承和創(chuàng)新。總的來看,其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
2.1 歸檔概念不清晰,范圍不明確。在實際傳承與保護(hù)中,有些工作人員缺乏對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檔案的正確理解,未能從非遺文化資源的內(nèi)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確歸檔范圍。[2]
2.2 在檔案管理制度建設(shè)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遺文化檔案的收集、歸類、整理、鑒定、保管等方面,缺乏專門人員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規(guī)范,工作機制被動,與文化部門、檔案部門協(xié)同機制欠缺。
2.3 缺乏規(guī)范的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評定標(biāo)準(zhǔn)。構(gòu)建科學(xué)合理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是納入規(guī)范化檔案管理的前提。盡管當(dāng)前相關(guān)部門也出臺了非遺文化檔案保護(hù)政策,但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還未全面執(zhí)行,特別是在管理辦法及實施細(xì)則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工作處于被動狀態(tài)。
2.4 對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重視不足。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保護(hù)與檔案管理,未受到社會公眾普遍關(guān)注,也未能受到相關(guān)部門重視,使得歸檔保護(hù)工作停滯不前。
2.5 硬件設(shè)施條件不足、安全性較低。河南省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保持條件較差,以鐵皮柜為主,缺乏防火、防盜、防霉、防水、防蟲等,有些地方的非遺文化資源僅存儲在電腦硬盤中,有的缺乏備份,電子檔案一旦丟失,其損失難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滯后,缺乏專業(yè)性。在信息化技術(shù)條件下,其檔案管理數(shù)字化工作相對滯后。如何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多樣化管理,如何推進(jìn)非遺文化
資源數(shù)字化宣傳,迫切需要信息技術(shù)支撐,提升非遺文化工作人員專業(yè)水平。
3 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原則
針對學(xué)術(shù)界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的討論來看,王云慶提出“做好非遺文化檔案管理,應(yīng)從建檔上堅持真實性、完整性、系統(tǒng)性原則,以分級保護(hù)、優(yōu)化利用為基本原則”;[3]孫展紅提出“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應(yīng)‘依項建檔、分級建檔和搶救性建檔’”。[4]根據(jù)我國檔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分級管理”原則,從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實際,應(yīng)該堅持以下原則。
3.1 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在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中,政府要發(fā)揮自身協(xié)調(diào)作用,加強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的統(tǒng)籌規(guī)劃。如針對當(dāng)前重復(fù)建檔、檔案工作評定標(biāo)準(zhǔn)不一致,缺乏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機制等問題進(jìn)行專門協(xié)同解決。
3.2 分級管理。對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采用全部移交給檔案機構(gòu)進(jìn)行保管并不現(xiàn)實,一方面與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特殊性有關(guān),另一方面與現(xiàn)有檔案機構(gòu)人力、物力條件有關(guān)。因此,從非遺文化資源保護(hù)與歸檔上,對于瀕危資源要歸口于檔案機構(gòu),對于衍生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應(yīng)根據(jù)分級制度進(jìn)行歸檔管理。
3.3 依項建檔。對于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在保護(hù)與檔案管理上,應(yīng)該根據(jù)“項目”劃分,進(jìn)行歸口管理。1998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人類口頭和非物質(zhì)遺產(chǎn)代表作條例》中提出兩類劃分,一類是民間傳統(tǒng)文化,如語言、音樂、文學(xué)、游戲、禮儀、神話、建筑藝術(shù)等民間文化形式;二類是基于“文化空間”的各類舉行傳統(tǒng)文化活動的場所,或定期舉行特定活動的時間等。[5]要根據(jù)各項目獨立設(shè)置,明確檔號,科學(xué)編制。
3.4 真實完整。堅持檔案管理的真實性、完整性是保證非遺文化資源檔案價值的重要原則。在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收集、整理、歸類管理中,確保非遺文化檔案信息、資源的真實性與完整。
4 河南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流程
4.1 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收集。從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形式的多樣性來看,在檔案收集上應(yīng)該拓寬途徑。一是開展檔案征集。由于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來源廣泛,對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遺文化要從征集公告、田野調(diào)查中主動收集;二是做好檔案接收。特別是協(xié)調(diào)好文化機構(gòu)、研究機構(gòu)與非遺文化檔案館的對接,完善非遺文化檔案保護(hù)與保存體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別是對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傳統(tǒng)民間文化資源,要從考證、挖掘、整合中發(fā)現(xiàn),加強保護(hù);四是接受捐贈。從非遺文化資源的歸屬關(guān)系上,尊重個人意愿專藏妥善保管,并對捐贈者獎勵;五是有償購買。通過平等協(xié)商,從非遺文化所有者手中計價收購并存檔保護(hù),對于重要的非遺文化檔案,要科學(xué)鑒定,保障檔案的價值。
4.2 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整理。在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中,要從檔案學(xué)理論與方法中,對收集的檔案資料進(jìn)行分類、組合、排列、編目,提升檔案材料的系統(tǒng)性、條理性,為科學(xué)保管和有效利用創(chuàng)造條件。如在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檔案管理中,注重檔案形成時間、檔案形式、檔案內(nèi)容的有機聯(lián)系,結(jié)合不同民間文學(xué)、傳說、故事、諺語等形式進(jìn)行歸檔整理。
4.3 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鑒定。根據(jù)語言文學(xué)類非遺文化資源特點,從鑒定方法、標(biāo)準(zhǔn)、原則等方面,確定其價值及保存方式、保存期限等。由于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種類繁多,對其存在形式及管理情況,要進(jìn)行科學(xué)化、專業(yè)化鑒定,為做好檔案管理把好關(guān)。針對不同載體檔案的特點,從保管環(huán)境如溫度、濕度等條件進(jìn)行科學(xué)管理。
篇4
關(guān)鍵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高校;保護(hù)傳承;傳播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1-0035-02
隨著日益頻繁的中外交流,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備受世界的青睞。我們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高校更應(yīng)該肩負(fù)起傳承中國文化、保護(hù)中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責(zé)任。
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概念和保護(hù)傳承價值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在歷史和自然的發(fā)展過程中,民間各種文學(xué)作品、技藝、工藝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場所等世代相傳的非物質(zhì)表現(xiàn)形式,是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學(xué)者王文章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概論》中歸納了非遺文化“獨特性、活態(tài)性、傳承性、流變性、綜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個特點。各地區(qū)非遺文化的合理傳承開發(fā),將使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融入現(xiàn)代社會,使非遺傳承人能夠保有持續(xù)弘揚甚至創(chuàng)新的動力,進(jìn)而使本土非遺文化成為地區(qū)社會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遺文化的保護(hù)傳承現(xiàn)狀
云南是祖國西南邊陲多民族大省,有著悠久的民族文化與豐厚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從2003年開始,云南作為全國試點省份,開展了民族傳統(tǒng)文化資源普查,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之后持續(xù)開展非遺申報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國家級非遺保護(hù)名錄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詩瑪、東巴造紙技藝、傣族潑水節(jié)、布朗族彈唱、普洱茶制作技藝、白族扎染技藝等107項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位列其中,有幾十個文化部命名的國家級中國民間藝術(shù)之鄉(xiāng)和中國特色藝術(shù)之鄉(xiāng)。同時,《云南映象》《云嶺天籟》等成為馳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懷秀、李懷福姐弟、香格里拉組合等,也成為云南原生態(tài)文化的代言人,這些文化遺產(chǎn)傳承與創(chuàng)新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遺文化傳承仍然存在諸多問題:
1.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律法規(guī)不夠完善,在城鎮(zhèn)化浪潮的沖擊下,云南不少傳統(tǒng)民居、服飾、語言習(xí)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貴的非遺文化亟待保護(hù)。
2.非遺基礎(chǔ)理論研究和學(xué)科體系建設(shè)滯后于保護(hù)實踐,各州市對非遺重要價值的認(rèn)識不一致、不到位,傳承人才隊伍參差不齊,非遺學(xué)科帶頭人和專業(yè)骨干匱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遺申報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諾族、德昂族等文化遺產(chǎn)亟待發(fā)掘和非遺申報。
4.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和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機構(gòu)之間還缺乏有力的合作機制,非遺傳承和保護(hù)形式較為單一。除了各級文化館、藝術(shù)院所是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主陣地外,還應(yīng)發(fā)揮博物館、研究機構(gòu)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遺保護(hù)及傳承機制多元化提高傳承保護(hù)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遺傳承保護(hù)的使命及文化責(zé)任
教育和文化傳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職責(zé)所在。當(dāng)年,西南聯(lián)大的聞一多、鐘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貴少數(shù)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非遺保護(hù)需要理論支持,理論研究正是高校的優(yōu)勢所在。作為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高校學(xué)者具有先進(jìn)的文化理念和很強的思辨能力,通過選擇、批判、傳承、傳播培養(yǎng)大學(xué)生的審美能力和宣傳文化保護(hù)傳承的責(zé)任意識,同時對傳承非遺傳統(tǒng)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創(chuàng)新的職能。
四、高校在傳承傳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經(jīng)驗優(yōu)勢,加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學(xué)科化建設(shè)步伐。
2.建立非遺文化保護(hù)人才培養(yǎng)計劃,構(gòu)建非遺人才培養(yǎng)機制,以老帶新,培養(yǎng)更多有志于從事非遺保護(hù)傳承專家和學(xué)人。
3.構(gòu)建高校、地方政府與傳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動教學(xué)模式。安排一名專業(yè)教師與一個非遺傳承人共同開設(shè)一門課程或講座。由傳承人現(xiàn)場表演,傳授藝術(shù)創(chuàng)作技藝、呈現(xiàn)創(chuàng)作過程,由專業(yè)教師從學(xué)術(shù)角度講授其起源、發(fā)展及流變,歸納藝術(shù)價值。這種通過口傳身授、聲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論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傳播弘揚非遺文化,也是對非遺傳承人一種長期良性的保護(hù)。云南財經(jīng)大學(xué)2016年就邀請一批非遺傳承人如楊文忠、畢向紅等到校開展系列“活態(tài)”非遺傳承活動,受到財大廣大中外學(xué)生的好評及政府管理機構(gòu)的關(guān)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園文化藝術(shù)節(jié)、“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日”以及國家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舉辦“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校園巡展”、非遺系列講座、學(xué)術(shù)論壇、“非遺”專題展覽和地方戲曲、曲藝、民俗游藝活動等演出,同時收集精品,通過走出去及網(wǎng)絡(luò)傳播的形式擴大傳播影響力。以此提升學(xué)生及公眾對傳統(tǒng)文化的興趣,深化大學(xué)生人文底蘊和人文情懷的培育與熏陶,打造繽紛多彩的校園文化。
5.搜集、整理有關(guān)云南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數(shù)字化資源,創(chuàng)建非遺名錄信息資料庫和研究資料專題數(shù)據(jù)庫,以云平臺資源庫形式用網(wǎng)絡(luò)傳播的渠道,將云南非遺文化傳向世界。同時,還可利用大數(shù)據(jù),對非遺媒體活躍度、關(guān)注度和成因進(jìn)行分析,進(jìn)而提出對應(yīng)策略,為非遺的活化傳播尋找方法和路徑。
6.隨著移動互聯(lián)時代的到來,對于引導(dǎo)公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對非遺文化的價值認(rèn)同,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應(yīng)在非遺文化傳播統(tǒng)一規(guī)劃體系下,通過網(wǎng)站、QQ、“三維一端”(微信、微博、微視頻、移動客戶端)等,以中英文雙語形式,加大非遺文化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和互動交流。
7.以產(chǎn)學(xué)研合作為載體,加強非遺保護(hù)與文化產(chǎn)業(yè)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多渠道為非遺傳承和弘揚提供持續(xù)的經(jīng)濟保障。
8.加強高校與博物館、文化館、專項科研機構(gòu)的聯(lián)合,形成資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遺保護(hù)既需要理論,更需要現(xiàn)場實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遺傳承保護(hù)應(yīng)在確定系列課題后,“走出去”主動融入非遺地進(jìn)行基層田野調(diào)查。云南財經(jīng)大學(xué)通過“布朗族彈唱”“傈僳族民歌傳承”等非遺田野調(diào)查課題研究,正在積累相關(guān)實踐經(jīng)驗。
10.非遺的傳承傳播應(yīng)在繼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斷創(chuàng)新,融入當(dāng)代民眾的文化生活。受到大眾的喜愛和維護(hù),才是最好的傳承保護(hù)。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資源,成立相關(guān)研究傳承機構(gòu)。基于此,云南財經(jīng)大學(xué)進(jìn)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會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傳承基地”,更加體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遺保護(hù)傳承和傳播中。
五、結(jié)語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將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保護(hù)傳承和傳播,并使非遺文化成為一種核心競爭力,是我們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責(zé)任和使命,也是進(jìn)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價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傳播引入高等教育體系,將豐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資源、教學(xué)手段及方法,也對高校大學(xué)生素質(zhì)教育起到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 王文章.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概論[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8.
[2] 劉寧.地方高校對本土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措施研究[J].大眾文藝,2014,(5).
[3] 李桂云,繆悅.學(xué)校教育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中的地位與作用[J].江蘇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13,(3).
篇5
一針一線,匠人精神
此次展覽,首次呈現(xiàn)了兩幅開創(chuàng)中國刺繡紀(jì)錄的巨幅高精繡藝術(shù)品:清代名家袁江的《阿房宮》和當(dāng)代著名山水畫家陳克永的《大壑騰云》,同時展出繡線細(xì)逾發(fā)絲的《維摩教演圖》等近40件不同風(fēng)格內(nèi)容的珍貴繡品,更有兩套80年代中國傳統(tǒng)的新娘嫁衣――殿堂級金銀線刺繡龍鳳褂裙。而參展的全部刺繡精品,均出自名瑞中國刺繡研究中心負(fù)責(zé)人、中國刺繡研究學(xué)者蔡民強與李春亮之精心設(shè)計創(chuàng)作。此次展覽,將兩位來自廣東潮州的刺繡藝術(shù)家推至公眾眼前,更從一個國家的層面深度詮釋了“工匠精神”的內(nèi)核與氣質(zhì)。多年來他們走遍了全國各個繡區(qū),從數(shù)百個手工刺繡坊中挑選出近幾十位巧手繡匠,親力親為出題材、制畫稿、組材料、定繡色、提針法,歷時五年多研究出品數(shù)百余幅手工刺繡精品。展品內(nèi)容之豐,涉及人物刺繡、動植物紋樣、自然風(fēng)光等多種題材;繡技之高,集中國刺繡的亂針、平針、圓針、釘針等多種繡法于一體,實現(xiàn)“去派別化”,推動刺繡藝術(shù)的融合發(fā)展。“我們希望留存下來,走向世界的,不是某一方面的繡種,而是中國刺繡的集大成者。”蔡民強說。
作為資深刺繡專家,蔡民強40年來潛心刺繡技藝研究,他攜手摯友李春亮先生,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現(xiàn)代中國刺繡藝術(shù)”的新概念,運用現(xiàn)代科技手段,融通各大繡種針法,歷時四年時間,創(chuàng)作出100多幅全新風(fēng)格的高精繡品,不斷推動這門針尖上的國粹傳承創(chuàng)新,走向當(dāng)代藝術(shù)繁榮的頂峰。
中國刺繡,世界之觀
“進(jìn)入展覽大廳,我屏住呼吸,很震驚,在這些作品面前我很渺小,在這些文化精華面前我變得渺小,刺繡藝術(shù)在中國經(jīng)歷一個又一個世紀(jì)的傳承,今日她現(xiàn)代化,她的顏色更絢爛,畫面震撼人心!”2014獲法國文化部騎士勛章的曼儂艾拉?皮拉教授(Manoel PILLARD)激動地說到。本次活動吸引了諸多中法重要媒體到現(xiàn)場進(jìn)行采訪報道。除了新華社、歐洲時報、新歐洲戰(zhàn)報、法國華文衛(wèi)視等駐法媒體外,環(huán)球時報、羊城時報、廣東電視臺等重要媒體還專門派出記者從國內(nèi)遠(yuǎn)赴巴黎進(jìn)行專訪。
巴黎中國文化中心主任蘇旭稱贊道:“這是巴黎中國文化中心十幾年來最好的一次展覽。”法方多名嘉賓表示:“中國刺繡這項特殊的藝術(shù)對于時尚界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國家要注重保護(hù)、傳承和創(chuàng)新,與時尚相結(jié)合。這個展覽令我們太震撼了,我們從沒見過如此精美的刺繡。
中國刺繡是我國重要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之一,推動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非遺文化走出去,讓世人看到她的精彩,通過展示中國刺繡藝術(shù)的歷史傳承與當(dāng)代創(chuàng)新,傳遞中國文化的內(nèi)涵與魅力。
“創(chuàng)新,永遠(yuǎn)是藝術(shù)發(fā)展的源泉。”蔡民強認(rèn)為,一個新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必然是這個時代嶄新科技與藝術(shù)的結(jié)晶和反映。在眾多繡品中,巨幅《阿房宮》對蔡民強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這幅由12條通屏組合而成的繡品,猶如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在這幅繡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藝術(shù)家的匠心巧思與新時代的科技手段緊密結(jié)合,擦出了令人驚嘆的火花。
《阿房宮》長6.52米,寬1.92米,尺寸遠(yuǎn)遠(yuǎn)超過其他繡品。蔡民強和李春亮用了9個多月的時間探索作品的雛形,特制了兩邊長度超過8米、重達(dá)100公斤的繡花架,并花重金定染了一整套耐磨度、色牢度、耐曬度均達(dá)4.5級的高標(biāo)準(zhǔn)繡花線。借助高科技,《阿房宮》整體上氣勢恢宏,局部則刻畫入微,將原作華貴綺麗的畫風(fēng)表現(xiàn)地淋漓盡致。《阿房宮》的問世,也讓蔡民強充滿了信心,“我相信,隨著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繁榮、紡織技術(shù)的發(fā)展,我們完全可以創(chuàng)作出像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圣彼得堡博物館的巨幅油畫一樣大小的刺繡作品。”